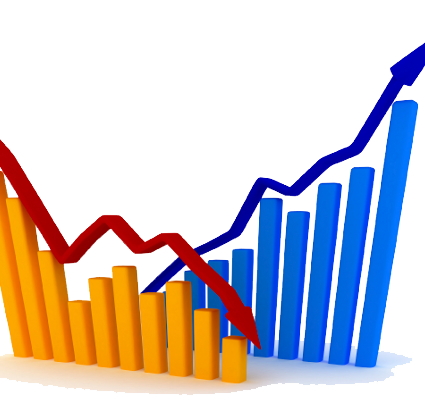我們一定要帶小孩去波蘭─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ly 30,2019人本愛智之旅

【愛智之旅──波蘭】
波蘭人知道:「寧可選擇危險的自由,也不要平和的奴役。」唯有持續追求自由,才能讓心智存活。
曾經,波蘭是歐洲大國,然而,近兩百年來,從封建邁向現代的過程裡,她特別坎坷。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波蘭終於重獲獨立成為共和國,然而考驗並未停止:經濟困難、政治失靈;本來這些考驗都可設法面對,但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波蘭人又開始起義抗暴。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走了納粹、來了俄共... 名義上,波蘭是個國家,實際上則被蘇聯控制、閉鎖於鐵幕;直到1989年──由造船廠工人帶領的「團結工聯」,以選舉的方式擊垮波共政權,促成了柏林圍牆的倒塌、蘇聯帝國的解體。
現在,後共產的波蘭,還有著許多挑戰,但現在的波蘭,可以為自己選擇行動的方向、努力的步驟。通往自由的路,非常漫長,但唯有如此可以保有人們追求幸福的選擇。
人本愛智之旅粉絲頁 https://pse.is/G4QL6
我們一定要帶小孩去波蘭
◎ 史英
我和小語從桃園機場出來,開上高速公路。經過市區的時候,他看著窗外,悠悠地說:「我們的國家怎麼會這麼醜。」我吃了一驚,這傢伙從來就沒有什麼「眼光」:把自己房間的「市容」弄到沒有人敢踏進一步,是媽媽長久的抱怨──我於是盤算著,等一下「歸還」小孩的時候,就先拿這件事情來講;也許就此可以扳回一城,如果又講到「幹嘛帶他去波蘭」的話。
其實小語的這種「比較之心」,自踩上異國之地從來就沒放下過,只是之前似乎未曾涉及美學。那天在克拉科夫(Kraków,波蘭王國舊都)的主廣場(Rynek Główny),聖瑪麗亞教堂(Kościoł Mariacki)塔樓上的喇叭聲剛停,他就跟我說:「這裡好像到處都有過去牽著你。」是因為他聽說了那個「塔樓號角」的傳統始自中世紀還延續到現在?還是這城市整個的氛圍讓他深有所感,感到我們在台灣的人心裡好像缺少一份歸屬。

這個話題有點沉重,所幸我們很快就到了雅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可以追尋哥白尼在校園裡走動的身影。那是一四九一年,還有六十年利馬竇才會出生,還有一百六十年鄭成功才會去台灣,而哥白尼就進來唸書了;專攻天文學嗎?不,他學的是藝術,而且,準備當神父。哇,真的是有夠過去的「過去」。看了在「哥白尼室」展出的手稿,我們說不出話來;我問:「這個過去怎麼會牽著(照你說的)現在的人呢?」他答非所問:「走進台大,會讓你想起誰?」我無語,總不能說是想起管爺吧?
他看出我的尷尬,連忙轉移話題:不管地動或不動,我唯一想不通的是,為什麼有人會去追究這種無聊的問題?我們在哥白尼紀念碑旁坐下,看著那人手拿渾天儀高高站在上面;我拿出口袋裡的詩集,恰好翻到〈在一顆小星星底下〉那一首,於是唸道:
我為稱之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誤謬之處,我向必然致歉
…
我為將新歡稱為初戀向舊愛致歉…
典型的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波蘭詩人,一九九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句法,蘊涵著一股莫名的情緒和力量,不由分說地牽著你。隔了五百年,這回是一九四五年,辛波絲卡進到這所學校;專攻波蘭文學嗎?是的,但後來轉去社會系。小語說:她一定也從這裡走過,也和我們一樣認真看著那座哥白尼;只是︱是因為這樣,她和鄭愁予或余光中就會那麼高下立判?(行前他已讀過辛的詩,而鄭余的詩都曾收入國文課本)
我疑惑地看著他,他就解釋:「新歡和舊愛那句我還看得懂,必然和巧合就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然後露出促狹的臉色,再加上一句:「難道哥白尼和她說了什麼暗語?」
我知道這是個「即景」的玩笑,但其中也未必沒有一些意思,於是說:看到宇宙萬物都繞著自己轉,順著自我中心的想法,於是視之為必然;這樣,就忽略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也許轉動的不是萬物,恰巧只是自己(例如,自己恰巧站在一個「繞軸自轉」和「繞日公轉」的地球上)。有了這一番頓悟和自省之後,不是照課本上說的「三省吾身」以免「一錯再錯」,而是,直指本心,覺得自己這樣偏愛必然,豈非欠巧合一個道歉?︱這種境界,正是你那個高下立判的感受的根源。
小語笑得很大:「被你說的,還真像有那麼一回事。」我也笑著:「其實,思考必然與偶然的對立、與關係,本來就是西方哲學的一個深奧的傳統,辛波絲卡和哥白尼,理當都受到這個傳統的影響;這些事情,長期在『中華文化』熏陶下的人很難想像…」
離開古城之後,我們去了華沙(Warsaw,波蘭首都),一路尋訪居禮的足跡,但蕭邦則是無所不在,想不遇到他都難。皇家瓦津基公園(Łazienki Królewskie)那座雕像真的很巨大,臉側向一邊,身體向後斜傾,衣衫隨風飄起,就那麼定在那兒;既不正襟危坐,也不揮劍或揮手,但最重要的,小語說:「他不是蔣介石。」然後,音樂會就開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陽光之下,草地之上,圍著蕭邦坐著;一個接一個的鋼琴家,在蕭邦的腳下的小棚子裡,彈奏蕭邦。
小語說:「怎麼雨滴還沒來?」我一時被騙,還抬頭望向天空;等聽到〈雨滴〉了,才想到他說的是第十五號〈雨滴〉前奏曲。但小雨說:「和霍洛維茲(Vladimir Samoylovich Horowitz,上世紀最重要的鋼琴家之一)彈的不同。」我吃驚地轉向他,他又露出促狹的樣子:「我是說和家裡音響聽的不一樣(並不是能聽出演奏家的差異)。」我轉移話題:「那麼,〈雨滴〉是你最喜歡的嗎?」他說:「其實,我比較想聽那兩首協奏曲。」好吧,這算是對我安排的行程的抗議:不去音樂廳,當然就沒有交響樂團的協奏!
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問他:「聽了音樂,你有感覺到他的『愛國情操』嗎?」他說:「心在祖國就好(蕭邦遺囑要求把心臟運回波蘭,我們今天才去過安置心臟的聖十字教堂Bazylika Świętego Krzyża),至於音樂嘛,好聽才最重要。」後來,我們又談起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波蘭科學家,鐳的發現者,兩次獲頒諾貝爾獎)。小語發表他的高見:「我當然認為應該稱呼她『瑪麗雅.斯.克.沃.多.夫.斯.卡(艱難地唸出來)』,至少在正式文件上不能只稱『居禮夫人』,姓居禮的人那麼多,誰沒有一個夫人?」如我所料,他果然接著說:「不過」︱不過,我真正關心的是,大家都只講她提煉新元素多麼辛苦,卻不講她是怎麼想到要去找新元素…」(這和放射性強度的測定有關,我和小語就此有許多討論,在此略過)
但我念念不忘在「克拉科夫城」的那個沉重話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會說:「台灣人缺乏歷史歸屬感,可能跟我們是一個移民社會有關,還有…」但小語打斷我的話:「你講的那些都不重要了,我們同學都認為台灣根本不可能再撐很久。」我大吃一驚,這些傢伙心裡想的,遠比我以為的更沉重。
走著走著,我們再次經過畢索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波蘭政治家,一九一八年帶領波蘭從一百多年的列強瓜分中取得獨立)廣場,悶聲不語許久的小語突然說,而且說得很大聲:「這次回去,我要跟他們講波蘭的事情,包括怎樣亡國又復國好幾次,最後還能把蘇聯老大哥趕出去;過程雖然很混亂,情節雖然很複雜,但我都知道了,知道得很清楚,誰也別想再騙我,騙我說台灣不行…」我別過臉去,沒讓他看到我眼眶裡的淚水。
終於到家了,「歸還」小孩的時候,我當然講了很多,講最多的,當然就是「別想騙我」的那一段;當然的,無論是孩子媽或爸,都再也沒提「為什麼帶他去波蘭」的話。
但是,從小語家出來的時候,卻換我心裡一直嘀咕著:「到底為什麼帶他去波蘭?還有,為什麼是帶他,為什麼是他──他誰啊,他憑什麼獨享這一切?」於是我們決定,這個暑假,一定真的要帶小孩去波蘭,帶很多台灣小孩去,安排更好的行程,讓更有活力的老師帶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