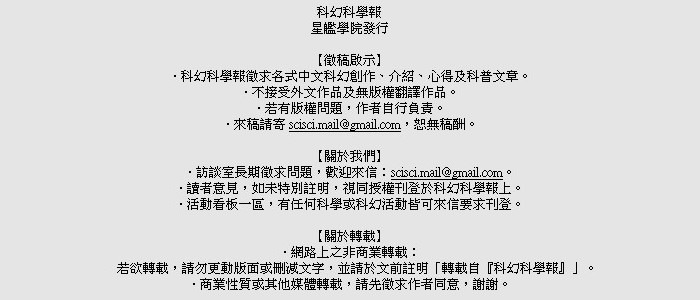【科幻科學報 No.571】《死亡遊戲》書摘─科幻科學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ugust 01,2017科科書介 ■ 《死亡遊戲》書摘
▌文/丁丁蟲
▌提供/貓頭鷹
1
七月的新上海,天氣格外的熱。上午七點剛過,太陽就從地平線上惡狠狠地跳出來,把存了一個晚上的光線一股腦倒在毫無遮擋的柏油馬路上,唯一可以聊作安慰的是路邊好歹還算有點遮蔭的地方,比如車站旁邊就生著幾棵小樹,不過那都是馬路拓寬之後新栽下去的,比一次性筷子粗不了不少。原先這裡倒是生了一排一個人抱不過來的大樹,據說都是長了將近百年的,可惜這些老樹都在城市道路拓寬工程裡給砍了個精光。
老剛沒站在樹蔭裡。等車的人挺多,先來的幾個年輕人已經占了那一點少得可憐的樹蔭,老剛也就不想去和他們擠在一起,寧願多曬曬日頭。時光倒轉五十年,自己曬日頭的時候難道少了麼?
車來了。剛一進站,還沒停穩,車站上的人便一窩蜂湧了上去。
老剛猶豫了一下,一個人慢慢退到樹蔭下面。
他捨不得坐空調車。
坐一趟普通公交車只要一塊錢,坐一趟空調車要兩塊錢。還是省省好。
旁邊有個老人也踱了過來。他和老剛一樣,都穿著件洗的發黃的白襯衫,下身穿著條藍布褲,腳上是一雙草綠色的解放鞋。這老人的頭髮也是剃得短短的,一根根朝著天豎著,其中大半都白了。看起來怕是不比自己年輕啊,老剛心裡想。
「報名去啊,老伙計?」那個老人站到樹蔭下面,從上衣口袋裡掏出塊手帕,擦了擦額頭的汗。那手帕是用毛巾裁的,洗的乾乾凈凈,邊上還細細橇了一道邊。大概是兒媳婦給做的吧,老剛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裡自己的手帕。
「嗯,是啊。你也是?」
「到哪兒報名?寶興殯儀館?」
「嗯……是啊。」老剛回答的時候猶豫了一下,他到底還是不習慣把殯儀館三個字掛在嘴邊。
「寶興館不錯,」老人沒注意老剛的猶豫,自顧自地往下說,「收費不算高,服務也不錯,我聽老鄰居的孩子說了,他們館裡的一條龍服務論項目不比外面的少,論價格可比外面便宜多了,到底是新民黨辦的實事項目啊。就是有一樣,太難考了。我去年考過一回,都過了統燒分數線,可還是沒給收進去。不過話說回來,我要是去年給收了,現在還能跟老哥你說話嗎,哈哈。」
「哈哈,哈哈,」老剛附和著笑了幾聲,笑聲落在自己的耳朵裡,都覺得乾澀得很。他問,「那你是去哪兒?」
「我去城西的普陀殯儀館,聽說那邊人少,可就是服務不怎麼樣。什麼壽衣壽褲都要自己穿好了進去,價錢也貴,一個小告別廳半個鐘頭就要三百點,唉,我跟兒子說了,我要是考上了,一不要遺體告別,二不要保存骨灰,都沒意思!有啥意思?都是虛的!難不成還想轉生再活一回?可你說但凡對世道有點留戀咱還能自己尋死麼?給孩子們多留點錢才是硬道理,老哥你說是不是?」
「你也是重孩子的人啊。」
「那當然了,不然誰考它個雞巴!自己找根繩子勒死拉倒,多省事!不就是想著自己蹬腿容易,剩下孩子們可就要受苦了,這才受它的鳥氣去報名考試幹這堆爛事嗎?不過話說回來,這些小子一個個都沒良心的很,你拚死拚活考一個火化名額出來,誰感激你?一個個都說你是自己找死──你說,我又不是腦子有毛病,要是能活得好好的,我幹嘛找死去?」
老剛點點頭,正要說點什麼,抬頭剛好看見又有兩輛汽車開進了站。前頭一輛是空調5路車,後頭一輛正好是老剛要乘的13路普通車。
「呀,老伙計,我的車來了。你坐哪趟的?」
「我坐是坐5路車,」老人看看前頭那一輛車,搖搖頭,自嘲地笑了笑,「不過空調車就算了。能省一點算一點,老哥你說是不是?」
2
早上七點出門,坐一個小時的車趕到寶興殯儀館,排一個半小時的隊領報名表,花半個小時找寫字的地方,再排一個小時的隊交表。一直弄到將近中午十二點,老剛終於把報名的手續辦完了。
殯儀館報名處還是黑壓壓的人山人海,都是花白頭髮的老年人,很少有年輕人在。也是,年輕人都要上班掙錢,也只有像老剛這樣退休了好久的老人才有大把大把的時間浪費在排隊報名上。
老剛從人群裡奮力向外擠,雖然報名大廳裡開著空調,可等老剛擠到門外也已經一身的汗了。他在一棵梧桐樹的樹蔭下面站了一會兒,喘了會兒氣,從上衣口袋裡掏出手帕想要擦擦臉,不小心把口袋裡的老人證帶了出來,啪嗒一聲掉在地上。老剛彎下身子,撿起地上的老人證,在大腿上撣了撣灰,翻開綠色的小本子,看看裡面的紙條還在不在。
老人證的全稱叫做「六十歲以上老人優待證」,早幾年坐公交車憑這個證可以免費的,不過這幾年公交制度改革,把這項優惠取消了。老剛之所以天天把這個證帶在身上,只是因為他把兒子的聯繫方式都給記在紙上放到它裡面了。萬一自己出門的時候遇到什麼意外,路過的人至少總能知道該給誰打電話吧。
老剛看過紙條還在,把老人證放回口袋裡,然後把手帕攤開,仔仔細細擦了一把臉。這手帕也是用毛巾裁的,洗的乾乾凈凈,邊上也細細橇了一道邊,不過不是兒媳婦做的,是他老著臉求門口做裁縫的小媳婦給做的。說起來也不是兒媳婦不給他做,只是媳婦工作忙,而且又剛懷了孩子不久,不忍心再給她加事情。唉,自己為子女著想,誰又為自己著想,可憐天下父母心啊——老剛這時又想起早上碰見的那個老伙計,在心裡把沒來得及說的話給補上了。他又歇了一會兒,然後咬咬牙,一頭扎進火辣辣的太陽光裡。
到車站的路似乎比來的時候要長許多。老剛好容易捱到車站,正看見有輛普通車進站,老剛趕忙跑了幾步,搶在關車門之前上了車。車門哐當一聲在他身後關上,差點夾住他的腿,然後還沒等老剛站穩,汽車就猛地發動起來,幸虧老剛及時伸手拉住了扶手,這才保持住平衡沒有摔下去。
車廂裡倒還不算太擁擠,只是座位都給坐滿了。老剛隨著汽車的顛簸一點一點蹭到老弱病殘專座前面,這位子上坐著一個小傢伙,大約是趁著放暑假出去玩兒的,看見老剛上來,趕忙把頭扭著向窗外,閉上眼睛養起神來。老剛見慣了這一幕,倒也沒覺得有什麼不滿,只是拉住了欄桿,任著汽車顛簸著。
汽車終於到了站,老剛正要下車,可是剛走下一級台階的時候就覺得腿上軟軟的沒什麼力氣,等到一條腿踩在地上,另一條腿還在車上的時候,老剛的腿不知道怎麼就突然軟了下來,恰好這時候汽車又猛地向前一衝,老剛的身子被汽車往側面一帶,一下子撲倒在地上,然後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3
下午一點來鐘的時候,病房裡面靜悄悄的。老剛斜躺在床上打瞌睡,迷迷糊糊的也不曉得睡了多長時間,倒是接連做了好幾個夢,其中只有一個夢老剛記的清楚,在夢裡他又回到年輕的時候,扛著槍正跟著連隊往敵人的陣地上衝,不知道怎麼一轉眼周圍就全沒了人,光是子彈在自己耳朵邊上嗖嗖地亂飛。老剛正摸不清方向,忽然腳下絆著個什麼,低頭一看,是自己連隊的指導員倒在地上,老剛趕緊俯下身子扛起他往回跑,跑著跑著,腿上一疼,就像給個大錘子狠狠砸在腿上一樣,連自己帶身上扛的指導員都摔了下去。
老剛猛地醒了過來,身上粘粘的出了一層汗。那一次他正是大腿上挨了一槍,硬是靠一股精神把指導員背下了戰場。後來戰地醫院的大夫說,幸好那一槍沒傷到骨頭,不然拖著一條腿走上好幾里路,他這條腿可就廢了,更別說還背著一個人了。
正在這時候,病房外面忽然嘈雜起來,像是有什麼人在外面起了爭執似的。病床上躺著的人紛紛醒了過來。靠門邊的一家的兒子站起來,輕輕開門溜出去,只留下一道小縫,外面的聲音就從門縫裡傳進來。老剛隱隱約約聽見似乎是有個人在哀求著醫生,說著什麼「大夫,您不能寫啊,我求求您了,您可不能這麼寫啊」,然後又有一個聲音,估計是醫生的人回答說,「你別跟我磨蹭,早幹什麼去了!你叫我不寫,我能不寫嗎?!這麼多人都看著,我不寫,給舉報了我是要受處分的!」
先前求醫生的人好像也說不出別的什麼,只會一個勁的懇求著說,「大夫,行行好,不能寫啊,寫了我們這日子還怎麼過啊。」
老剛沒聽見醫生再說什麼,只聽見腳步聲急匆匆地從門口過去,漸漸遠了。再過一會兒,靠門邊的那家的兒子悄悄溜了回來。病房裡一群人全都圍了上去。
「怎麼回事?外頭怎麼了?」
「唉,還能怎麼回事,死了一個唄。」
「死了?在醫院裡?」一群人面面相覷,臉上都掛起了物傷其類的不安。
「那死了人的這一家,有沒有考個名額出來?」
「怎麼可能考出來麼——你們也都聽見剛才那家人怎麼求大夫的了,這家人要是有名額,至於求成那樣嗎?」
「哎呀,沒有拿到名額就死了,這家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呀?」
「該怎麼過怎麼過,最多當年社會補助降級唄。」
「你說的輕巧。要是當年一年就好嘍,是連續十年!」
「十年?這麼長?」
「是啊,而且每年都按最低生活保障線的標準來,不管你原來是什麼級別。」
「這麼厲害?我一直以為是一年,而且是只降一級……話說回來,你們家的都考出名額來沒有?」
這個問題提的似乎有點不合時宜,病房裡剛剛還熱熱鬧鬧討論著的人們,一時間全都安靜了下來。老剛本來躺在一旁的病床上,並沒有加入到其他人的討論裡去,可是聽到鄰床的家屬提起名額的事,心裡也是咯噔了一下子。
自己的名倒算是報過了,可真能考出個名額來麼?
4
老剛下了電梯,兒子和兒媳都跟在後面。到從掛號廳裡出來、下台階的時候,兒子搶上來,把手上的袋子都並到一起,騰出一只手,攙住老剛。老剛忍了許久的火一下子冒起來,他猛地一甩手,罵道,「老子不用你扶!」
「爸……」
「我跟你說我自己能走,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老剛一面大聲罵著,一面自己騰騰騰走下去。兒子不敢再伸手,只好跟在後面走下去。老剛一口氣往前走,眼看走到醫院門口的時候,終於覺得自己的氣實在喘不上來了,不得不停下來喘一會兒氣。
這時候太陽正從對面的樓房後面照過來,在老剛腳前映出一道黑黑的邊。老剛微微抬起頭,瞇著眼睛往對面看,只見馬路對面是一堵牆,牆後是一座嶄新的高樓,那是新華東醫院的幹部病房。大樓的外牆鋪著光潔的大理石,上面鑲著「新華東醫院」五個大大的金字。金字的旁邊從樓頂往下垂著一條大紅布條,布條上寫著「熱烈祝賀由本院黑信求恩教授主刀的本市首例多器官移植手術圓滿成功」。
「娘西比!」老剛罵了一句從部隊裡學來的粗話,「圓滿成功圓滿成功,你們他媽的賺了老百姓多少黑心錢?!」
正罵著的時候,前面馬路上突然拐進來一輛車,是輛黑色的東方紅,司機顯然沒想到醫院門口會站著人,猛地一個急剎車,車輪擦著地面,帶著刺耳的噪音又向前衝了好幾米,最後將將在老剛面前停了下來,好歹算是沒碰到他。
老剛的兒子和媳婦都嚇了一跳,急忙搶了上來,老剛自己也嚇得不輕,他定了定神,指著車裡的人大聲地罵,「你他媽怎麼開車的?到醫院裡還開這麼快,你不想活了?!撞死人你給償命啊?!」
兒子叫了一聲「爸」,插進來問,「你沒事吧?」
老剛搖搖頭。他罵的急了,有些喘不上氣,便住了口喘了一會兒,卻看見東方紅後排的車窗給搖了下來,從裡面探出一張臉,臉上和自己一樣布滿了皺紋,也長著不少老人斑,頭髮卻不像自己的花白,還是烏黑烏黑的,臉上的氣色也是不錯的模樣。這張臉盯著老剛看了一會兒,忽然喊了一聲,「是剛志武嗎?」
老剛愣了一下,仔細端詳著探出車窗的那張臉,猛然間想起自己住院的時候做的那個夢。他試探著問,「指導員?」隨著這一聲喊,他看見那張臉上的皺紋都皺起來,這才興奮地叫起來,「指導員!真的是你!指導員!」
「是啊,是我啊,自從你退了伍,咱們有多少年沒見了?說起來,我這條命還是你給揀回來的啊。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三十年前失去聯繫之後就沒了你的消息,沒想到今天在這裡遇上了,咱們今天要好好聊聊,好好聊聊。」老剛的指導員越說越激動,看樣子就要從車上下來,可就在他打開車門的時候,前面的司機扭過頭攔住了他。
「首長,您和醫生約好的時間……」
老剛聽到司機的話,登時明白過來,趕緊接上去說,「指導員,約好了時間還是快去吧,如今的醫生一個個難伺候的很,讓他們等久了可沒有好話聽。咱們另找時間聊就是了。」
老剛的指導員看看司機,又看看老剛,點了點頭,說,「那好吧,」他向著司機說,「小李,把我的地址和電話給——」老剛的指導員頓了一下,「我是該喊你老剛了吧?哈哈,記得以前在部隊的時候,我一直小剛小剛的喊你,想不到一晃這麼多年過去嘍,你這當年的小傢伙,頭髮也白了啊。」
老剛的胸口像是堵著什麼東西似的,一時說不出話來。憋了半晌才說,「你看上去倒是還年輕,一點都不顯老……」
這時候司機放下了車窗,從窗口遞出了一張名片。老剛接過來,轉身交給兒子,讓他好好收著。
「你兒子?不錯不錯,都長這麼大了。」
老剛說,「快喊伯伯」,兒子有點不好意思地叫了一聲。
「嗯,嗯,」指導員一面點著頭一面說,「有空多聯繫,咱們找個時間好好聊聊。」
司機按響了喇叭,東方紅朝著嶄新的高樓緩緩開去。火辣辣的陽光照在鏡子般光潔的黑色車身上,把站在車邊注視著汽車開動的老剛晃得睜不開眼睛。
5
臨近吃飯的時間,老剛坐在客廳的沙發裡,半閉著眼睛聽著電視裡新聞聯播的聲音。電視上正放著新聞概要,先是一個柔和的女中音在說「中科院克隆人培植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成活率已超過百分之七十七」,然後換作男中音說「和諧社會建設再結碩果,人口死亡率又創新低」──「娘西比!」老剛忍不住罵了一聲。新聞裡說起來總是輕巧的很,可又有誰知道死亡率新低的背後是多少辛辛苦苦地捱著日子過的老傢伙?
「爸,」兒子推門進來,還在門口的時候就先喊了一聲,「有你的信。」
「我的信?」老剛應了一聲,心裡有點奇怪。他從兒子手裡接過信,隔著鏡片,看見那是個大號的牛皮紙信封,信封上貼著一張白紙,白紙上打印著自己的地址。
「大概又是什麼假藥的廣告吧,這年頭,假藥廠比老子自己都清楚我家的地址,」老剛一邊嘀咕,一邊撕著信口。牛皮紙的信封挺結實,老剛撕了好幾下才撕開。
信封裡面的東西讓他怔住了。
掉出來的是一張賀卡一樣的硬版紙,版紙的外面是漆黑的顏色,四周都燙著金邊,版紙中間浮版凸著五個字,也是燙了金的,寫的是:
火化通知書
老剛急急翻開內頁,只見裡面是雪白的紙,紙的四角印著菊花的圖案,雪白的紙片中間用漆黑的鉛字赫然印著:
剛志武同志,我們嚴肅地通知您,您在二○四六年度火化資格考試中的成績到達了和諧殯儀館的火化分數線,獲得了在和諧殯儀館實施安樂死並火化的資格,特此通知。請在二○四七年三月三日前攜本通知書、戶口本及本人身分證來我館辦理相應手續。有關事項詳見後頁說明。
在這一段文字後面是一個黑黑的公章,「新上海市和諧殯儀館」幾個字圍著公章的外圈排成彎彎的一道。
「這、這是怎麼回事?」老剛盯著手裡的紙看了半晌,好容易才擠出一句話。
「爸你不是去考試的嗎,考過了就有通知書啊。」
「通知書?我都考砸了,怎麼會有通知書給我?而且我報的是寶興殯儀館啊,怎麼寄了一張和諧殯儀館的火化通知給我?」老剛自言自語著搖著頭,「古怪。這通知書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無意中抬起頭,卻看見兒子臉上不自然的表情,而且一和他的目光接觸,兒子就匆忙轉過了臉。老剛頓時明白了。
「是你小子搗的鬼?」
「沒……沒有。」
「沒有?還跟老子撒謊?!老子現在打不動你了是不是?好,你不說實話,老子就撕了這張破紙!」老剛一手抓住通知書的一頭,往兩邊用力,打算把這張紙片給撕開,可是手上到底沒什麼勁,撕了一下沒能撕動,反倒因為用力過猛,忍不住咳嗽起來。
兒子急了,撲上來攔住了他。
「別,爸!不能撕!」
「不撕?好,那你說,這到底怎麼回事?」
「好,我說就是了……是我託了關係,想辦法幫你要了一個名額。」
「好、好、好,你小子也學會托關係了,」兒子的回答果然和老剛預料的一樣。他氣極的時候反倒笑了出來。「你小子托了誰的關係?」
「爸,你還記得夏天住院的時候遇上的指導員嗎?他留過一個地址,我就是去找了他。那個指導員雖然已經退了,可還是離休幹部,而且他的幾個兒子都在要害部門工作。我去找了他,跟他說了爸你的情況,他當時就給開了條子,還專門給殯儀館打電話,說你是他的老戰友,一定要給你安排一個名額。爸,你的這位老指導員人果然是軍隊上退下來的,一點官架子都不擺,還說出殯的時候他要親自來……」
兒子正在喋喋不休地說著的時候,老剛突然伸出手去,在面前的茶几上重重一拍。
「混蛋!你求誰都好,怎麼能求我的老指導員!當年我在部隊裡,就是他教育我,這世上數當官的最髒,你去求他,不是給我丟臉嗎?!」老剛看看手裡的通知書,把它往茶几上一扔,「不行,這個通知書我不能要。我要去和老指導員說,我不要他寫條子,我要憑自己本事考出來!」
「爸!你這又何苦。你那個指導員已經不是當年在部隊的那個人了!他自己的孩子哪個不是靠他的關係混到要害地方的。而且他現在連整個人都——」說到這裡的時候,兒子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收住了話。
老剛問,「都什麼?」
兒子搖搖頭,「沒什麼,反正就是告訴你,他不是從前那個指導員了。」
老剛被兒子說的一怔,想了想才說,「人家怎麼樣我管不著,可我不能這麼幹。」
「你要這麼說,那我當年考大學的時候你不是也找過你們廠長想辦法?」
「我那是為了你上學,不是為我自己。」
「那我就是為我自己啊?」
老剛冷笑起來。「把自己爸爸想方設法送進火葬場,這難道還是為了我好?」
「不為你又為誰?你以為你去報名中暑的時候我心裡好受?你以為你天天敖夜看書的時候我一點都不心疼?你要不想要通知書,當初幹嘛要去報這個名?」
「不報名,我這病你有錢治啊?上次中暑才住了幾天,扣掉咱們家多少錢?不報名不考試,我們一家人一起等死嗎?」
「是啊,就是這個道理啊,那我托關係又有什麼錯?我不也是想讓家裡人過好一點、想讓你老爺子活著的時候多過幾天好日子嗎?」
老剛被兒子搶白的一時不知道說什麼才好。兒子接著說,「爸,不是我心狠,一定要送你去火葬場,實在我也沒有辦法。你從小教育我要遵紀守法,可這個世道我不偷不搶就只能掙到這麼多錢,現在的三級生活水準也是拚死拚活才掙到的,可你現在又查出來肺病——」
「肺病?」老剛第一回聽說自己有肺病。「什麼肺病,都是醫院嚇唬人的,好從你口袋裡摳錢。我抽了那麼多年的煙,肺當然不好。我現在不是戒了煙了嘛……」
「不一樣的,」兒子之前說漏了嘴,索性一並說了出來,「醫生查出來你得的不是一般的肺病,名字怪的很,反正就是很難治療的病。醫院你也是知道的,不管什麼病,真要到了不得不住院的時候,不弄得傾家蕩產不會放你出來,而且就算傾家蕩產也不見得能給你治好。萬一你真在醫院裡走了,咱們家可就要給打回最低一級去,到那時候我們可怎麼辦?你也知道你兒媳婦快生了,到時候真讓你的孫子跟著民工的小孩一起上幼兒園、上小學?爸,別的都不說,我和你兒媳再怎麼受苦都能忍了,可總不能讓孩子一生出來就受苦吧,爸?」
兒子說到後來,聲音都有些哽咽了。老剛一開始還是氣鼓鼓的,可漸漸地也不知道究竟該說些什麼了。他默默地聽著,伸手把扔在茶几上的通知書重新拿起來。老剛的這雙手拿過機槍、拿過手榴彈,甚至還拿過敵人的刺刀,可是他以前拿過的所有東西,似乎都沒有黑色版紙上那幾個燙金的字刺人。
(未完,全文見倪匡科幻獎作品集《死亡考試》,由貓頭鷹出版。)
科學小視窗 ■ 日本東北又有7.1強震
▌文/科科報編輯小組
日本3/11大地震剛滿月,昨天日本東北部又發生規模7.1的強烈餘震,引起許多民眾驚慌。
根據外電引述美國地質調查所資料,這個淺層地震震央位於福島縣磐城西南方22公里處。磐城是位在發生核災的福島核電廠南方。日本原子能安全局說,7.1餘震後,冷卻3座反應爐的注水作業停止約50分鐘,不過對安全沒有影響。
日本氣象廳指,3/11發生規模9.0大地震後地盤鬆動,仍可能發生較大震度的餘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