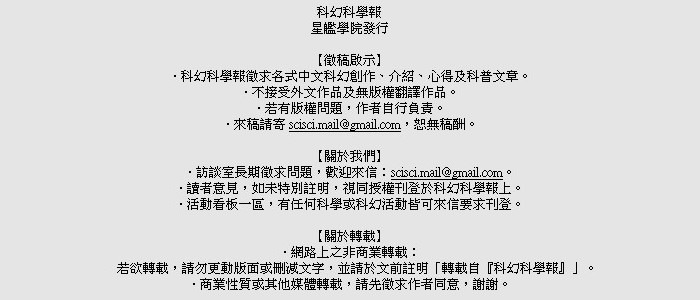【科幻科學報 No.647】演化超級人類─科幻科學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ugust 01,2017最IN話題 ■ 演化超級人類
▌文/薩波斯基(Robert M. Sapolsky)
▌譯/林慧珍
▌提供/科學人
如果你有機會與人類學家一同坐下來談論人類本質,很可能會聽到這個老梗:「嗯,你要知道,人類歷史的99%都是在遼闊的稀樹草原上度過,靠著小規模的狩獵與採集維生。」這是個經典的科學老生常談,也是事實。確實,老祖宗數百萬年的漫長生活促成了我們許多的招牌特徵,例如直立行走與更大的腦。當然,這些超級有用的演化新招是有代價的:雙足站立會背痛;較大又能自省的大腦皮質讓我們產生絕望感。演化往往就是這樣,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我們所創造的這個世界,混雜了這些利弊得失的挑戰(以人類悠久的歷史來說,這也只是最近的事情而已),已經與以往身體與心智所適應的那個世界大不相同。晚餐變得唾手可得(多虧有外送服務),不再需要追逐覓食;登入臉書就能與最親近、最摯愛的人互動,不必一輩子把每天的大部份時間都用來跟他們相處。但是,人類學家用來解釋人類處境的陳腔濫調就到此為止。
我們在新時代面臨的處境,已經與人類力圖演化適應的環境大不同,原因是人類有另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關鍵特徵:人類有衝動想要超越演化的限制,並發展各種工具使我們更快、更聰明、更長壽。科學就是工具之一,它是一種創新,需要我們打破在石器時代「眼見為憑」的心態,好除掉下一個即將面臨的障礙,可能是流感爆發或是氣候變遷。我們或可稱之為人類的極致表現,是人類精益求精的獨特本能。
人類的特異之處
為了解天擇如何把我們塑造為獨特的靈長動物,讓我們回到祖先的稀樹草原。這種開闊的地形,與我們的猿類祖先稱之為家的森林截然不同。稀樹草原的驕陽炙熱無比,營養價值高的蔬果食物也比較少。為了適應這樣的環境,我們的祖先脫去厚重的體毛以保持涼爽;他們不再只吃粗硬的蔬食,也開始吃草食動物的肉,於是臼齒越來越小,如今這些臼齒變得用處不多,表面幾乎沒有研磨功能。
同時,為了應付食物短缺,我們祖先的身體逐漸變得極度節能而且善於儲存熱量。現在的我們,繼承了同樣的新陳代謝模式,卻大口吃著漢堡、喝可樂,結果使糖尿病成為世界性的災難。或者試想,在一個難以遇到新病原體帶原者的環境,我們的免疫系統也不會有什麼演進,但如今,如果你在機場某個人身旁打了個噴嚏,不用到第二天,你的鼻病毒可能就散佈到12個不同的時區。
人類的行為更有許多特異之處,身為靈長動物,很多方面與魚類或鳥類有極大的不同。例如特別有趣的是,靈長動物一般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一種是單一配偶(pair bonding)的物種,也就是雌性與雄性組成穩定、長期的配偶,行一夫一妻制的社會與性關係。一夫一妻制的雄性通常會擔負一些或甚至大多數的育幼工作,而且這些物種的雌性與雄性體型相當,外貌也非常相似,長臂猿與許多南美洲的猴子就是這種模式。另一種「比武式」(tournament)的物種則採取相反策略:雌性負責所有育兒工作,雄性的體型比雌性大得多,而且身上有各種豔麗的炫耀展示,例如華麗又醒目的臉部色彩和有光澤的背部,這些好鬥的雄性把多到離譜的時間花在展示挑釁的姿態。後來,人類出現了,他們在解剖、生理甚至遺傳上的各種手段,既不像傳統的單一配偶制,也不像比武式,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
然而人類也表現了另一種典型的靈長動物行為:我們具備強烈的社會性,社交是我們最高明的智慧。身為靈長動物的我們,有時候可能會困惑於某個複雜的遞移數學難題,但卻能輕易理解如果某甲比某乙優勢,而某乙又比某丙優勢,那麼某丙在遇到某甲時,最好卑躬屈膝。我們能夠領會非常複雜的社交情境,也能理解某個社會規約受到違背(而且察覺某人行騙的敏感度勝過注意到某人特別慷慨)。我們的臉部辨識能力更是所向無敵:人類腦部的梭狀回(fusiform gyrus)甚至還有專門負責顏面辨識的皮質區。
高度社會化大腦的天擇優勢很明顯,人類能夠藉此微調我們讀取他人心思的能耐、專精於社會操縱,並熟練地欺騙或吸引可能的配偶與支持者。美國年輕人的社會智力比SAT成績更能準確預測他們成年後在職場上能否成功。
事實上,談到靈長動物的社會智力時,人類拔得頭籌。靈長動物演化的社會腦假說,就是建立在各種靈長動物之間,新大腦皮質在腦中所佔的比率與該物種平均社群規模的關聯性。人類社會展現的關聯性(以傳統社群規模來看),比其他靈長物種更緊密。換言之,人類大腦中最獨特的區域,是與各種人類關係的需求共同演化,包括誰跟誰已經不是同一夥、誰現在位居優勢階級,或者哪兩個不該在一起的人正在廝混等。
我們的大腦與行為就像身體一樣,也是在過去古早的狩獵採集生活下逐漸形塑而成,一樣必須適應截然不同的現代環境。我們能夠在離出生地千里之遙的地方生活,我們能夠殺死不曾謀面的陌生人,我們在迪士尼樂園排隊玩太空山時遇到的人,遠比我們祖先一生中遇到的多。我的老天,我們甚至可以望著照片裡的某個人並產生情慾,卻連這個人聞起來是什麼味道都不知道,以哺乳動物來說,這是多麼奇怪?
超越演化極限
我們創造了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世界,而且活得很好,這證明了一個重點,那就是我們的天性不受自我天性的束縛。我們對於超越界線一點也不陌生,人類試圖挑戰祖先的極限,科學是其中最奇特、最新穎的領域。我們的世界裡最引人注目的轉變,就是科學的直接產物,其中的挑戰也不言而喻。只要想想試圖馴化某些植物與動物的遺傳學家就好了,他們的發明使糧食產量大幅提升,現在卻讓地球面臨自然資源耗盡的威脅。
從抽象的層面來看,科學也在試煉我們對於標準的概念,怎樣才算比較好。它挑戰著我們的自我感覺,拜科學之賜,人類壽命不斷延長,我們的平均身高增加了,標準智力測驗的分數也提高了。拜科學之賜,每一場體育賽事的世界紀錄最終都會被打破。
隨著科學把這些領域的極限向外推展,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變化對我們產生的改變卻如此渺小。無論我們的壽命能延長多久,終究難逃一死,還是會有一個死因,我們還是會覺得親人太快蒙主寵召。一旦人類平均變得更聰明、更高大、在田徑場上表現得更好時,問題來了:誰還在乎平均如何?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比別人好,我們的大腦是愛炫耀、愛比較的,對於勝過別人的興趣大於勝過自己。這種心態源自我們的感官系統往往不是辨識某個刺激的本質,而是相對於周圍的其他刺激。例如,視網膜中的細胞對於單一顏色的反應,不如兩相「對比」的顏色(例如紅色與綠色)那麼敏感。與其說我們都希望自己很聰明,不如說我們多半只想比別人聰明。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運動員,這就引發了一個人類老祖宗的切身問題:被獅子追的時候要跑多快?而答案始終是:比你旁邊的人快就夠了。
儘管如此,面對各種待解問題時,科學多半會促使我們超越限制,這有四種特定的類型。第一種類型與科學中常見的反社會特性有關,我指的並不是某些類型的科學問題需要獨自鑽研,科學家常在凌晨三點還任勞任怨獨自工作。我的意思是,科學通常促使我們對了無生氣的東西產生極大的興趣。這個規則顯然有許多例外,例如靈長動物學家老愛在半夜圍坐閒聊著各種猴子的弱點與瑕疵;古生物學家李基(Louis Leakey)總是把他最喜愛的頭骨化石稱為「親愛的男孩」。然而,某些科學領域思考的卻是沒有生命的議題,例如天文物理學家試著找尋太陽系以外的行星。科學往往促使我們這個社會化的人類大腦熱中於一些非常不可能的議題。
當我們在思考量子力學、奈米科技及粒子物理等問題時,必須相信眼睛看不到的東西,此時,科學是以另一種方式把我們推出框架。念研究所的那幾年,我總是把液體從一個試管吸到另一個試管,測量激素及神經傳導物質的濃度,如果我當時曾經停下來想一想,可能會認為液體中根本沒有激素或神經傳遞物。這種不真實感,就是為什麼很多像我們這樣在實驗室裡測量、複製或注入看不見的物質的科學家,會覺得徒手玩乾冰時最令人興奮。
科學本質上能產生許多問題,這是第三種把人類推出想像邊界的方式。當回憶遙遠的過去,或談到對未來的感覺時,我們在動物裡是無與倫比的。但這些技能有限,傳統上,從事狩獵採集生活的人類祖先可能記得祖母告訴他們、流傳自祖母的祖母的事情,或者他們可能曾經想像死後一或兩個世代的事情。但科學有時要求我們思考會隨時間而發生卻沒有先例可循的過程。下個冰河期何時會到來?剛瓦那古陸會再度合併嗎?100萬年後,蟑螂會統治我們嗎?
人類的心智會質疑怎麼有這麼長的過程,也不會認為這過程很有趣。我們與其他靈長動物都是沒有耐性的動物,立即得到10塊錢或10顆猴子飼料,比明天拿到11顆更有吸引力,大腦造影實驗顯示,在我們追求衝動性的立即獎賞時,大腦中的多巴胺報償迴路立刻亮了起來。大多數人似乎寧願在下星期就得到半盒不新鮮的爆米花,也不想等待1000年才贏得對板塊構造假說的賭注。
最後一種能讓我們超越極限的科學問題,是對各種眼花撩亂的抽象概念感到困惑: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意識是怎麼運作的?世界上有不可能了解的事情嗎?
人們確實相當容易被某個簡單的見解吸引,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心智放棄了這項挑戰,只用神來解釋一切。問題出在我們對創造之神的想像各有偏好(例如有宗教信仰的個性孤僻者,心目中神的形象往往也是不合群的,他們最關心的是原子如何聚集之類的問題)。在人類發明神的歷史中,沒有一種神明對抽象概念有強大的理解力,相反的,祂們沒多大興趣。傳統的神不會想與數學家哥德爾一起閒扯「知」的意義,也不會想跟愛因斯坦一起丟骰子(或是不丟骰子)。祂們還比較熱中於得到最大的獻祭牛隻,或是能與最多的森林仙女勾搭。
科學的過程不把人類的極限當做一回事,它要求我們專注於很小甚至看不見的東西、不會呼吸或移動的東西,以及在空間及時間上距離我們非常遙遠的東西。它鼓勵我們關心那些雷神索爾或魔神巴爾覺得無聊到不行的事物,這是我們所創造的事情中最具挑戰性的一項。難怪當我們在閱讀《科學人》之類的雜誌時,有些人會大驚小怪。從事、思考、關心科學的投資,並不是因為懦弱(我們對此的適應力比面對劍齒虎時好太多了),我們藉此重塑世界,並努力改進我們生命中的科學問題,這就是我們人類的本質。
(本文原載科學人2012年第127期9月號)
科學小視窗 ■ 研究發現抗藥蛋白可與單股DNA結合
▌文/科科報編輯小組
台灣的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王惠鈞研究團隊,日前以表皮葡萄球菌為研究對象,發現表皮葡萄球菌內一種名為TcaR的關鍵抗藥蛋白,可以與單股的DNA結合,並進一步抑制DNA的複製過程,這項發現改寫以往學界認為此類的抗藥蛋白只能與雙股DNA結合的主張。
中研院指出,這項刊登在國際期刊《PLoS One》上的研究,將提供研發抗生素新的思考途徑。研究團隊解釋,通常表皮葡萄球菌的細胞壁遇到刺激,例如抗生素的殺菌作用時,細胞壁外會形成一層生物膜,而抗藥蛋白TcaR即是操縱生物膜的關鍵因子,透過抗生素操控TcaR與DNA的結合,開啟或關閉生物膜的生合成。
這次研究團隊配合電子顯微鏡,以及「流動式生物感測系統」與「圓二色偏光儀」等技術的分析,發現TcaR在一般狀態下,會與雙股DNA交互作用,然而在細菌體內單股DNA濃度昇高時,TcaR會轉而與單股DNA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