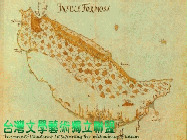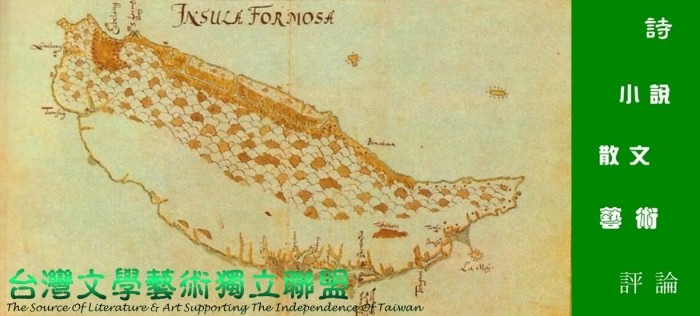多樣語言的文學價值─台灣文學獨立聯盟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ne 22,2011邱一帆─留下來(liuˇhaˊloiˇ)
留下來(liuˇhaˊloiˇ)
天公還在頭林頂
tienˊgungˊhanˇdo teuˇnaˇdangˋ
面項抹上
mien hong madˋsongˊ
賁賁个烏雲
punˊpunˊge vuˊ iunˇ
烏疏疏个塵灰
vuˊsoˇsoˇge ciinˇfoiˊ
看毋著半點
kon mˇdoˋban diamˋ
穿入个光線
conˊngib ge gongˊxien
Ngai問自家
ngaiˇmun cii gaˊ
落泥時就在這位
log naiˇsiiˇqiu coiˊliaˋvi
淨一隻身兩支腳
qiang idˋzagˋsiinˊliongˋgiˊgiogˋ
這時節
liaˋsiiˊjiedˋ
Ngai愛離開
ngaiˊoi liˇkoiˊ
抑係留在這位
ia he liuˇcai liaˋvi
穿入个光線
conˊngib ge gongˊxien
看毋著半點
kon mˇdoˋban diamˋ
賁賁个烏雲
punˊpunˊge vuˊiunˇ
滿奈仔烏疏疏个塵灰
manˊnai eˋvuˊsoˇsoˇge ciinˇ foiˊ
離開
liˇkoiˊ
烏灰共樣還在
vuˊfoiˊkiung iong hanˇcoiˊ
ngai還係愛留下來
ngaiˇhanˇhe liuˇhaˊloiˇ
撥烏雲
badˋvuˊiunˇ
望春光
mong cunˊgongˊ
......網路閱讀
5656─紀錄
紀錄
一本一本的筆記簿
寫著夢想的詩句
愈寫愈無意思
置空白的所在
貼一張最近才歙的相片
發現阮置阮的面飼兩尾魚
拖著長長的魚尾溜
◎註解..
置→在,台語音ㄉ一
歙相→照相
......網路閱讀
蔣為文─陳芳明們,不要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難!
陳芳明們,不要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難!
--再度回應陳芳明的謬論
在母語文盲陳芳明教授還沒學會台文書寫之前,本人仍將權宜地使用中文回應陳芳明的謬論。
近日發言污名化本人並認為母語文學會「窄化台灣文化」 (聯合報)且「堅用台文恐失溝通平台」 (公視)的政大台灣文學所所長陳芳明今日來到國立台灣文學館參加鹽分地帶文學研討會的圓桌會議。在提問期間,陳芳明不僅不正面回答現場多人針對母語文學的質疑,還刻意分化族群和諧,實令人感到遺憾與不可思議。
不僅地球暖化,人為因素通常也是造成生態失衡的主因。不當的引進外來物種通常是造成本土物種滅絕的原因之一。譬如美國大螯蝦、福壽螺與紅火蟻等都對台灣的生態造成嚴重破壞的後果。外來物種並非不能引進,但必須在對當地物種不構成生存威脅的條件下,逐步與本地物種形成生態平衡才行。若因引進外來物種而造成本地多數物種死亡,這絕對是災難,而非生態多樣。
隨著地球自然生態受破壞事件日益增多,世界文化多樣性也遭受空前的浩劫。本人深信,台灣文學絕對是多元文化的文學,包含原住民族語文學、客語文學及台語文學。即使是華語、日語、英語及越南語等台灣國民使用的語言,當然也可以成為台灣文學的一部分。但,如果台文系(所)必須獨尊華語,這絕對是霸權心態,而非多元文化的表現!
如果陳芳明真的是文化多元主義者,就應該展現在台文所的專業設計。可惜,從政大台文所的設計,只見獨尊華語,卻不見台灣母語文學的蹤跡(參閱圖一)。譬如,碩班入學考寧可考國文、英文及中國文學史,卻不容台灣語文。畢業語文寧可要求第二外語,卻不屑台灣語文。試問這樣合理嗎?英文系加強英文,日文系加強日文,中文系加強中文,台文系加強台灣語文,這本是專業訓練應有的分工合作。可惜,陳芳明卻假藉文化多元之名,行霸凌台灣語文之實!
我在此鄭重呼籲陳芳明們,立即停止製造台灣文學生態災難,讓台灣文學回歸真正的多元面貌吧!
圖一: 政大台文所ê專業訓練設計
|
|
台灣語文課或母語文學課 |
碩士班入學考科目 |
博士班入學考科目 |
畢業語文要求 |
|
政大台文所 |
無 |
1. 國文 2. 英文 3. 台灣文學史 4. 文學理論與批評 5. 中國文學史 |
1. 專業外文 2. 台灣文學史 3. 文學批評 |
1. 英文 2. 第二外語 |
......網路閱讀
胡長松─張德本《累世之靶》中的歷史、族群與美學特點
張德本《累世之靶》中的歷史、族群與美學特點
1 前言
近年來,筆者一直在族群神話與自我圖像的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當代的台語文學[1],我認為族群的母語文學不僅要反映出族群精神歷史的腳跡、命運,也呈現出族群自我的追尋與盼望。重要的是,自我的神話不只是文字的紀錄,它們甚至要為族群自我生命的發展做出指導。2010年,詩人張德本先生所完成的這首規模約莫2500行的長詩《累世之靶》,無疑是這個自我追尋的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成果。此外,無論從神話學本質與詩的技巧來看,這首詩都和當代文學所側重的反諷(irony)有極深的關聯:在文字的背後,本詩是對台灣歷史長年受宰制命運的形而上的反思,它透過詩句逼問每個台灣人:「在歷史面前,作為一個台灣人的意義何在?」光憑這一點,我們就要鼓勵每個台灣人都來讀讀這首詩。
因為這首長詩的規模龐大豐富,我的這篇文章自然無法論及它全部的要點,所以,也只好從我的管窺心得整理一二並進行簡單的分析,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2 從Sanasai談起
在認識這首詩之前,我們首先應該留意一件事,即Sanasai 的意義。這首詩的第一章以Sanasai為題,最後一章也以Sanasai為題,可見Sanasai這個字在這首詩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當然,若我們進一步研究,就會發現Sanasai這個字對台灣而言有一個起源神話的意含:
Sanasai傳說是二十世紀初,日本調查者伊能嘉矩、波越重之、移川子之藏與馬淵東一等人,在台灣從事原住民神話、傳說、歷史及氏族系譜調查時,分別於明治、大正或昭和年間(約1895到1935的四十年間),在台灣的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從阿美、噶瑪蘭、馬賽等族群的長老村落身上,採集到的傳說故事。
換句話說,Sanasai傳說是流傳於淡水河流域、北海岸、宜蘭平原到花東海岸原住民世界中,一個有關祖先來源、移動和定居的故事。
這些故事,雖然主題都是Sanasai傳說,但由於採集時間、地區和受訪對象的不同,內容卻相當多元,大家說的都有些不一樣。
儘管如此,如果異中求同,我們仍然會發現有一些基本元素是存在於每個Sanasai傳說中的。以下,我們先對故事的原型做一個基本的介紹:
昔日有一群人,因為家鄉生存不易,所以離開南方島嶼──有的會說這個島嶼的名字就叫Sanasai──的故地,往北遷徙。在移動過程中,人們先到一個名叫Sanasai的小島落腳,再以這裡為根據地,分別往台灣東海岸的某處登陸。之後,或者就此定居,或者繼續沿海岸,往更北方移動,尋找可以長久居停下來的地方。 (引中研院平埔文化資訊網)
簡單講,Sanasai,可能就是台灣人最原始的自我認同的精神核心,對台灣人而言,這個字牽涉到台灣各族群的起源神話,也可能就是各族群的「名中之名」。詩人在詩的開頭幾行這麼寫:「Sanasai!/佇毋知名的南方/閣卡遠的東南方/閣卡遠的飄洋中的/東南方………」便是源於上述的台灣口傳的起源神話,詩句透過海浪般一波一波前進的自然節奏,將「南方」與「飄洋」的想像連結,整合了詩的形式與內容,使得這首思索台灣命運的長詩的最開頭,被賦予了一個海洋神話的印象;而這個海洋神話的源頭,在經歷了2500行的詩行敘述,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時空疊遞之後,至詩的最末尾又歸回到「Sanasai」的呼喊──這在詩的敘述結構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彷彿在提醒台灣人:我們當代台灣人的生存,仍然未脫「Sanasai」這個海洋神話原型的精神核心;我們,仍活在Sanasai的海洋母親的命運暗示裡。因此,詩人在全詩的最後一段這麼寫著:「你(按:即Sanasai)是我的母土/我佇你歷史的夢中醒來/旅程的風景/已經有身/思念的內海/波湧日月的光耀/位這個島嶼/湧向世界的海洋………………」詩行如斯再次回到Sanasai,不僅是海洋神話原型的重現,同時更豐富了這個原型以「有身」、「世界的海洋」的族群繁衍與寬闊的希望意象,可說是非常精緻細膩的安排。
讀者們對於這個神話原型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這不僅是就神話學的意義而言,也是就這個原型本身對於族群命運的隱喻來說的。
所以首先我要先談談和Sanasai相關的神話學的意義,尤其是神話與族群生存、族群記憶之間的關係。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可先參考一些當代學者的看法。
比如《金枝》的作者、著名的人類學家弗雷澤(J. G. Frazer, 1854-1941),他的人類學研究是當代神話原型理論的先驅,他在其著作《舊約中的民俗》一書中談及世界各民族的大洪水傳說時這麼說:「雖然關於此類可怕大洪水的故事幾乎毫無疑問是傳說性的,但其中許多故事有可能並且實際上很可能在神話的外衣下包含著真實的內核。也就是說,它也許含有對確實發生在個別地方的水災的記憶……洪水把災難擴展得又遠又廣;倘若其中有些回憶在經歷過洪水的那代人的後裔那裡沒有留存很久,那才是真正的怪事。」[2]弗雷澤把神話與人們的真實記憶之間做了連結。同時,他在人類學研究中所發現的形態類型重複現象,也提供後來原型理論的基礎。
再者,同樣是人類學者的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在經歷了廣泛的田野調查之後這麼表示:「流傳於原始社會的神話,乃其原始真貌,故不祇是說來說去的故事而已,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它的性質,非係向壁虛構,如同我們今日讀的小說那樣,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體,相信曾在往古出現,自後一直對世界和人類命運發生影響。野蠻人心目中的神話,如同虔誠基督徒所深信的聖經故事,如創造宇宙、亞當夏娃誘食禁果、耶穌釘死十字架上等。我們的神聖故事,存在於我們的儀式及道德之中,於是支配我們的信仰,控制我們的行為;原始人的神話,亦復如是。」[3]此說法可說是對上述族群神話與記憶之間的連結做出了更深刻的闡釋。
再者,是精神分析學家榮格(Carl Gustaf Jung, 1875-1961),他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理論,提出了遠古人類社會就有一種經長期儲備的集體潛意識經驗,可以從夢境、神話或文學藝術(傳奇、詩歌、戲劇等)表現出來。也就是說,一個種族或集體的潛意識中,貯存著人類往昔的經驗與神話象徵,而且,就如同前述的人類學所觀察的一樣,它們時常會重複出現。因此,榮格也提出「原型」(archetypes)的概念,即指在藝術或文學中不斷重複出現的的意象、主題、人物類型或故事輪廓,這些「原型」都是來自集體潛意識。他的理論深化了神話與族群記憶/集體潛意識的關係,而成為當代神話原型理論的基礎。也就是說,當我們研究神話裡所隱含的「原型」的樣貌,我們也就有機會能解開裡頭的關於族群生存記憶和集體潛意識的關鍵。榮格所提出的原型包含了Mana原型、精神原型、Anima原型、Animus原型和(大地)母親原型等。就榮格的理論來說,本詩的Sanasai即是一個大地母親的原型,這個神話原型當然和台灣人往昔的起源、遷徙經驗深切相關。
又再者,文學批評家弗萊(Northrop Frye, 1912-1991)接承了弗雷澤與榮格在人類學與心理學中所發現的不斷重複出現的原型理論,擴大了原型理論在文學中的應用。他在1957年出版《批評的剖析》,受到了很大的注意。與榮格不同的是,他更著重於原型現象的歸納而較少談論成因(如榮格所提出的集體潛意識)。他認為各民族的神話一如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循環不息,亦擁有最顯著的不斷重複的原型現象,故理解某個神話的原型特性(形態類別),有助於我們認識這個神話的意義;此外,經過歸納,他認為即使是當代的文學作品也可用這個神話原型理論來分析。
以上略舉的神話學理論說明了神話對於族群生存的意義,在這裡我要提出一個簡單的看法,即,本詩的創作本身在當代原型理論裡可視為隱喻台灣人命運的現代神話,且這個現代神話的核心又包含了Sanasai這個遠古神話的元素,此神話元素從弗雷澤、馬凌諾斯基、榮格以至於弗萊的理論來看,都是代表台灣人起源與母地的象徵。所以,我們可以說Sanasai是本詩「神話中的神話」,它可能有台灣人古老的經驗與記憶在裡面。
正因為Sanasai在這首詩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我們要進一步看看詩人所建立(或重現)的這個原型的形象本身如何。
在歷史文獻裡,台灣原住民Sanasai傳說是頗多的,我在這裡先略舉一個阿美族的Sanasai傳說:
阿美族自稱祖先從外島移入的,有海岸阿美的大港口社;他們傳說祖先最初住在達奇里,後來遷移火燒島,然後在台東附近上陸,從海岸山脈西麓北進,迂迴太巴塱,才來到大港口建立部落。貓公社則自述祖先是從花蓮北方的達奇里來到Sanasai,再登陸大港口。都威社傳說天神降生於Votol,再經由Sanasai繁衍阿美族、卑南族、噶瑪蘭族子孫。都歷社則傳述Votol大地震後,從石頭生出阿美族、卑南族的祖先;祖先們經由Sanasai來到台東附近的猴子山,兩族在這裡再分化出去。[4]
雖然各族Sanasai傳說的細節有差異,但不難看出一些共通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族的故鄉在不知名的海外南方島嶼,遷徙是飄洋而來,而在遷徙過程中,或者經過名叫Sanasai的中途島,或者直接指稱原鄉就是名叫Sanasai的島嶼。[5]這個共通性相當程度地支持了台灣近代一些人類學家對於台灣人起源於南島的「南來說」的看法。張德本先生的這首詩顯然也採用了這樣的看法。在Sanasai神話的共通性裡,時常出現一對兄妹,他們是族群的始祖,而在這首詩裡就是Potsok和Raya,詩人這麼寫:
Potsok和Raya/赤身趴佇Tamima[6]頂/海湧千萬丈衝Tamima闖過沉佇海底的/Sanasai!/海洋的大漂流開始未知//毋知漂流過外濟層海湧/漂流過外深的海溝/漂流過外遠的日光月光佮星光//Tamima 偎岸佇大水中的島嶼/Kavorongan[7]/春天佮秋天共時臨世/夏天佮冬天同齊出現/毋知經過外久/大水纔漸漸消退/Kavorongan島嶼/續變做Kavorongan大武山
如是,以Sanasai為核心,將台灣的歷史時空拉回到太古起源之初,台灣人的祖先經過一波又一波的海浪,在大水的日子,從Sanasai飄洋來到了台灣南部的大武山。我們仍要用馬凌諾斯基的話提醒讀者,這個神話,「它的性質,非係向壁虛構」。張德本先生藉由這個神話的書寫,試圖重建台灣的族群起源記憶,當然其中包括了作為詩人的想像與詮釋。他在詩中怎麼詮釋這個起源呢?他寫著:
開始一切本正就無意義/意義佇無意中發現/島嶼發現海洋的廣闊/漂流發現原點的疲勞
我們在這裡讀到了一種反諷似的弔詭。一方面詩人把起源神話Sanasai放在詩開始的第一個字以表示重視,但一方面,在這裡卻又寫著「開始一切本正就無意義」。到底「開始」這件事有沒有意義呢?我認為這是詩人對於起源本質的一種形而上的辯證思索。對於人或者一個族群的起源,在開始的那一刻其自身是無從察覺意義的,但,若就某些時候來看則不然,這個意義就會在奇特的眼光中被顯現出來,以至「意義佇無意中發現」。例如在聖經裡,當亞伯拉罕生以撒時,他們還不能相信甚至明白他們確實是耶和華上帝所應許他們的「像天上的星那樣多」[8]的後裔的祖先,但到了今天,幾乎任何一個希伯來人都能清楚亞伯拉罕生以撒在族群起源上的意義。在高度壓縮的詩句裡,我認為「開始一切本正就無意義」近於反諷似的弔詭(paradox)即在於此:「開始」既是無意義的,也是有意義的。事實上,我們更能察覺出詩裡想要傳達的訊息卻是反面的──「開始一切正是意義的根本」,只是當事者自己在起初的一刻無從察覺而已,這也就是歷史的弔詭本質。那麼,詩人所謂的無意中發現的意義又在哪裡呢?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詩行發現線索:「島嶼發現海洋的廣闊/漂流發現原點的疲勞」。在詩人的眼光裡,這個起源神話隱喻著台灣人生存的命運,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我們的命運仍在島嶼與海洋之間探尋,在漂流與原點之間辯證。台灣人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這是詩人在這首詩的序章的一個形而上的提問,也是整首詩的核心問題──他要用整首詩來回答的問題。在序章的稍後,詩人如是地加強這個意義:
漂流答謝山脈/海湧的堅凍/山稜的走向/海水變動交換土地安定承擔
種粟答謝島嶼Votol[9]/粟是海洋浮出日光的黃金/位東方島嶼每日的黎明結晶出來/粟稻是飽足/保族的神使
從漂流中出現生命的起源,在海的不安裡尋找土地的安定,又在米稻的豐收裡繁衍生命,成為每日黎明的新結晶,是詩人對於台灣歷史起源的再一次形而上的演繹。這裡面有我們的悲傷,也有我們的歡喜;有我們的失落,也有我們的希望;有我們的軟弱,也有我們的堅定;有我們的威脅,也有我們的機會──簡單講,台灣人生存的自我意義就凝結在這裡,在古老的Sanasai,也在今天的Sanasai。
3 累世之靶是什麼靶
在這裡,我想對累世之靶做一個題解,故參考作者自述,對整體的長詩的內容做一個簡介。
本詩共計分為17章如下:
(一)Sanasai!無仝民族共同神話的母親
本章書寫Sanasai傳說,即許多台灣原住民族群共同流傳的起源神話,敘述民族的緣起,形塑創世紀開天闢地的原始氛圍。對台灣大自然海洋、島嶼、風火、寒熱漂流、寂靜、聲音等做形上思辨,意義在無意中發現,開啟一切的意義。
(二)「歷史的被告」真濟根本無欠貨!
本章以圓山貝塚、左鎮菜寮溪、台東長濱文化等歷史遺址的人類遺骨、獸骨、化石、陶片、石刀、石斧、石簇,證明五萬年前台灣就有先民生活居住。論述違背歷史遺址認知的人,是歷史審判的被告。表面不知台灣史的化石卻顯出歷史的真知,自然不會作假,化石的不齊全愈證明化石曾經完整存在過。
(三)大員第一王國—大肚王國
以「大肚王」及荷蘭的各相關台灣長官等為主述者,敘述荷蘭據台之前在台灣中部,以大肚、沙鹿為中心北臨大安溪,南界鹿港之間有一個跨族群,牽涉到Papora族、Taokas族、Babuza族、Hoanya族的王國,由King of Middag(即 Quata Ong大肚王或柯大王)統領二十五個村社,但不敵荷人、鄭成功、清朝的侵討,終究滅亡的歷程。
(四)雨落佇咱查某祖的腹肚頂
以Papora族Siraya族的歷史際遇,追溯台灣人平埔母祖的源頭,喚醒沉睡的血緣。以鹿皮、鹿肉、鹿骨、鹿角、鹿鞭象徵平埔先祖的被剝削的血淚。
(五)夢中佮阿立祖講話
藉九二一大地震隱喻平埔阿立祖還在台灣,辨證平埔語滅失、台語在日語、北京語殖民體制下的困境。呈現漢人壓迫平埔族的殘酷事實。
(六)早起想著朱一貴
由朱一貴的反清革命失敗對比如今台灣對中國的屈從,思辨民族的屈辱如何自省?屈辱是根,被壓迫深埋土底,發四百年傾斜的樹,像枝枒分杈的民族,結滿樹恥辱的果實,一代一代隨人劈扯。
(七)伯尼約斯基伯爵未完成的美夢
就伯尼約斯基伯爵在一七七一年無意中來到台灣東部的史實,辯證台灣在歷史中的艱難處境。伯尼約斯基伯爵可能改變台灣歷史,但志業未酬。
(八)赤日亂屠
描寫日本佔領台灣,簡大獅、柯鐵、林少錨、余清芳等台灣民族前仆後繼的抵抗,與日本利誘台奸及屠村鎮壓的殘暴。
(九)槍孔的回聲底時纔會當停止?
記錄二二八事件之後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獨裁政權對台灣人民的荼毒,至今和解未見曙光。
(十)以國為名實在是人世間的恥辱
論證詩,論盜賊被認做父母,以國為名,實是人世間的恥辱,地上的國度都是征戰得來的,桌上的食物都是血汗換來的,戰場上的屍體都是父母過去扶養的,我們以恥辱為名不感覺恥辱,我們永遠不放棄以擁抱為名。
(十一)日夜做累世之靶
本章是論證抒懷,也是這首詩的思想核心,辯證台灣的歷史存在有如累世之靶,承受千萬共業的注目,穿心的姿勢自毀雙目,凡人各執弓槍,出手不問任何理由。「萬彈穿射累世標靶,活靶倚立世間何種目標?活靶承受何等摧毀?活靶破碎眼目瞄射的一切完美,靶位變動甚麼不動?射手無靶一切都無法出手,無射手的靶,倚立還有何用?射手毀掉歷史之靶,靶解放一切射擊。」逼問台灣人如何自如靶的歷史中出脫而得真自由。
(十二)打造一枝tháu縛黑暗的鎖匙——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記錄早年廖文毅等在日本推展的台灣共和國獨立運動,將台灣人的自由心聲向國際呼喚的歷史。
(十三)鹽佮糖
從糖和鹽兩種深具台灣本土元素的產物,辯證台灣人的性格,結黨排他是歷史宿命,結黨總是糖多太甜,排他往往鹽多太鹹。台灣人如何在鹽與糖之間取得平衡?
(十四)洲子
以「洲子」淹在大水中,象徵台灣八十年代的處境,辯證農村、教育、認同、獨裁、民主等議題,自救是台灣唯一脫困的出路。
(十五)袜袂當醒袜袂當睏的時代
描述新世紀台灣的迷惘:「這是既能吃又能喝的時代/也是既不能醒也不能睡的時代//這是既能偽裝又能心安的時代/也是既不能堅持也不能放棄的時代//……一直在想這究竟是甚麼時代?/却始終有個聲音反問:/『你又算是時代中的甚麼?』」反省台灣人存在的時代意義。
(十六)泅是咱的活海
以鯨魚游向大海象徵台灣的活路,鯨魚上陸就是擱淺死亡,游是我們的活海。並以空氣、疆界的屬性辯證統獨,只有死亡是統一的,其他一切的生命,都因為分裂而延續。分裂即是生命,分裂即是自由,統一即是僵化,統一即是死亡。
(十七)Sanasai!你是我的母土
Sanasai!是台灣原住民族共同追尋的神話,台灣就是我們現實的Sanasai!是我們的母土,我們在歷史的夢中醒來,旅程的風景,已經懷孕,思念的內海,波湧日月的光耀,從這個島嶼湧向世界的海洋………………
綜觀之,我們不難發現,全詩採取針對台灣歷史順敘的結構,從起源神話Sanasai寫起,夾敘夾議地穿插安排,歷經考古石器時代、(與西方大航海及明鄭時代交錯的)平埔部族時代、清代、日治、二二八、白色恐怖、廖文毅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中國的威脅、一直到詩人呼喊「泅是咱的活海」傳達對未來的企望,最後回歸到Sanasai,湧向世界的海洋……如是縱寫台灣歷史的生成、挑戰以至未來的活路,可說是對台灣長久命運的全盤思索。對詩人來說,過去長久的台灣歷史,就是一長串遭受外力侵犯、威脅、剝削的歷史,就好像一個累世的靶,不問理由就被射擊,甚至反諷地好似靶是為了射手的射擊而存在一般。而我們的生存究竟在哪裡?
夾敘夾議是本詩的特色,詩人一方面用敘事詩的形式書寫台灣歷史(有時運用不同的主述角色),一方面也用詩句議論抒懷,上述歷史觀的體認,即在本詩第11章「日夜做累世之靶」的詩句中企達核心。在這一章,我們察覺到的是這麼樣的一種心情與體認:
聽不著的話語/永遠是新的/衫褲深藏衫仔櫃/無穿著毋捌展示過/全新的紅嬰仔/棉絲巾緊緊攬抱未來的人父人母/未看過凝視的眼眸/永遠攏是新的
這些詩句裡頭存著很強的挑戰性與思辨性,讓我們察覺一種心裡上的衝突:既是「話語」,又怎麼會「聽不著」?既是「新」,又何能說「永遠」?既是「衫褲」,又為何「無穿」?雖然從「棉絲巾緊緊攬抱未來的人父人母」這句我們似乎感受到一絲生生不息的下一代的希望,而且後來的二句「未看過凝視的眼眸/永遠攏是新的」似乎加強了這個希望,但,「凝視」這個詞卻又讓人不安。到底是誰的「凝視」呢?最後一句「永遠攏是新的」,表面上是正面的期待,但也隱含了「似乎永遠不會出現(才能保有『新』)」的絕望感。這是William Empson在《歧義七式》裡所提及的一種對立歧義,詩人很純熟地運用於此。在「永遠」與「新」之間,我們的歷史感知被凝結,這個凝結,促使我們反覆思索。這是一段成功的暗示性的開場。緊接在這段之後,詩人這麼書寫:
困獸的柵門無人敢開/時間的光催醒飢荒的大海/浪湧絞滾無法抵擋/波瀾已成娑婆/醒佮睏的岸到底佇何方?
前一段的不安被推向了現實與夢境的大洪荒。海在這裡象徵了外來侵略的歷史,在這裡是「時間的光」照徹下的威脅,是柵門後的困獸,一波一波湧來無可抵擋,猛回首波瀾婆娑。這是夢靨般的意象,而夢靨中如一波波海浪般湧來的侵略與威脅,從荷蘭人、明鄭、清國、日本、以至現代中國,未一刻稍減;綜合前段來解讀,一種如「全新的嬰孩」般清純且自由的生命何等美好,但在侵犯者一次又一次的凝視裡,這樣的「新」又何從誕生?「醒佮睏的岸到底佇何方?」帶出一種覺醒的眼光,這是一種對己身存在感的覺醒,在接下來的三段作出衍繹:
人子總是後悔錯過真濟想欲做的/也做過真濟後悔的/後悔所僭越的毋是全世界/後悔乞求所失去的尊嚴/後悔做過的一切/攏不如荒野上的一枝敗草
人母袂振動倒佇眠床/你為伊洗浴淨身的時陣/莊嚴看見你最初出發的所在/萎縮的兩腿中央/青春之花被死亡緊緊看守/處子無一絲絲皺紋的柔嫩……
人父真久毋捌講話/眾人以家己的意圖強解伊的意涵/不語挺逞掠奪/無言默許佔有/脆弱者攏無言語/深奧的意義攏佇言語之外/水火佇無情中/裂縫佇堅硬中/熔岩佇斷層裡/叛逆都無永遠/堅持那有永遠?
台灣人的存在,或為人子,或為人母,或為人父,在這裡並列,也在這裡對話,從外在的客觀歷史的關切轉而向內,成為對主觀的存在感的內在的觀照,歷史環境不再只是身外的客體,而是相對於人存在的處境(境況),詩在主客之間找尋一代一代生存的尊嚴與可能,在為人子的反省中,在面對前行代生命的消逝與脆弱之際,察覺出自身生命的局限,並從死裡見生,成為生命選擇投向的動力。這些詩句不僅是對台灣人存在感的觀照,也具普遍性,探索著身為人的存在本質,同時也為稍後的「革命者踦佇死亡隔壁/所以活咧!/革命者踏過死亡/所以活咧!」以及「種佇死亡中纔有真正的活咧」伏筆,互相呼應,整體來看,透露出沙特式存在主義的反抗觀,也概是整首《累世之靶》的心理基礎:在新生的期待中面臨絕望,卻又在經歷絕望後體認到選擇的可能而達致生存的突破。這個心理基礎,匯流出整首詩的精神核心:
日夜做累世之靶/承受千萬共業的注目/鑽心的姿勢自毀雙目仁/凡人各夯弓槍/出手無問任何理由
萬彈穿射累世標靶/活靶踦立世間何種目標?/活靶承受何等摧毀?/活靶破碎眼目瞄射的一切完美/靶位變動啥物不動?
射手無靶一切攏毋法度出手/無射手的靶踦立有啥路用?/射手毀掉歷史之靶/靶解放一切射擊
若台灣是靶,歷來的千萬射手「出手無問任何理由」,是否活靶只能命定要承受摧毀?假設這果真是命定,那麼,台灣是不是只能絕望?
這首詩的讀者可能要先回答這個問題:「靶位變動啥物不動?」是不是可以說:射手瞄準的凝視眼目不動?射手的意志不動?靶的身份不動?靶終將被摧毀的命運不動?若台灣是靶,我們還能逃避嗎?就算這是過去的歷史法則,我們除了被動的接受或逃避外,還有什麼突破的可能?
顯然,詩人是不甘於被動的,他要從否定的行動裡取得主動。「射手無靶一切攏毋法度出手/無射手的靶踦立有啥路用?」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反諷的心情,看起來是狀態的陳述,但也能是未來的企盼:透過否定與拒絕,抹除了靶的身份,就回歸到主體存在的第一個基礎,而這個說「不」的選擇,就是從死裡見生的超越。「射手毀掉歷史之靶/靶解放一切射擊」補充了這個超越的含意。這二句裡頭有多義歧義:第一義,是就過去來說,射手們毀掉了歷史之靶,但在靶被毀滅之際,這些射擊也因靶的毀滅被『解放』了;『解放』,暗示了射手的處境,在射擊前彷彿被什麼東西綑綁了,是慾望嗎?是優越自傲嗎?是貪念嗎?是自卑嗎?是一切無法抗拒的罪念嗎,以致就算是射手也無真自由可言?靶的毀滅反諷地成為射手的犧牲品與拯救者。第二義,我們也可以就未來來說,既然『靶』的存在會讓射手陷於慾望罪念的綑綁,那麼,只要把『靶』的存在(或身份)抹除,射手們也就會脫離罪慾,而將被解放。否定『靶』的存在,表面而言是反諷,但若從反諷的命運裡覺醒,在主觀上,就走向了對於命運「反抗」的意志。這二層複雜的含意被濃縮在二行詩句,透過岐義引人深思辯證,也足見詩人的功力。這二行詩的重要性,可視為解開整首詩的「詩鑰」並不過份,裡頭的精神,和前段提及的死裡見生的存在境況,自然是相承的,在積極面,以否定(或拒絕)作為靶的命運和處境,就是詩人在精神上的革命了。所以他接著說:
無欲反/即是無欲反省//無欲反/即是無欲改變//無欲反/即是無欲喘喟//無欲反/即是曝焦的魚//無欲反/即是規鍋滷汁//無欲反/即是永遠打袂開的門//
我們在此看見了詩人所企求的、對於未來的希望,都在「反」字上,反對接受現狀,反對歷史宿命,反對為靶的主體,而在這個靶的死滅中打開未來之門。我們題解至此,也終於比較能夠體會詩人為本章下結論的這幾行詩:
一切可能的名/攏佇所有名姓考慮之外/一切可能光明黑暗分界的地平線/攏佇凝視之外/一切袂當分身重現的形質之本/攏佇思想之外
在所有名姓考慮之外、在(他者的)凝視之外、在思想之外,存在著我們真正的自己,存在著我們自由無拘、且像初生嬰孩一般無所畏懼的心靈。
4 平埔認同書寫及史觀
從比例來看,本詩在「大員第一王國—大肚王國」、「雨落佇咱查某祖的腹肚頂」、「夢中佮阿立祖講話」等三章共計733行的篇幅直接書寫平埔族,若計未有文字記錄的前二章史前歷史書寫,篇幅更達到921行,所以,我們說這是一首以平埔認同為核心的歷史論述詩基本而言是恰當的。我們也發現,詩的其他篇章,也是在這個認同基礎下的歷史詮釋,這也是讀者可以留意的地方,比如在「以國為名實在是人世間的恥辱」,詩人寫著:「我的屍體排路邊/有人夯刀一塊一塊割/恁講生番肉好吃相爭買/有的買心臟做藥治腎氣病/我的膽值銀三十元/會當做刀槍傷的藥仔/有人干單欲買骨頭/焢膠做藥治寒熱病/阮全身軀攏有人買/干單大小腸頭毛無路用/恁講刣一个生番勝過打幾仔隻鹿/刣一个生番勝過一年冬辛苦種田」就是這個平埔認同的主旋律的呈現。簡單講,我們可以說這首詩是以一個平埔族的後代的身份寫成的,或者,從敘述理論裡,可以說這首詩的隱藏作者設定為一個平埔後代。不管作者真實的族群身世為何,這首詩呈現出詩人在身世認同上的一種決定,這個決定,本身也可看為前面提及的一種反抗精神的延續,而這個反抗的對象,就是基於平埔史觀而對漢人身份的拒絕的態度。
第三章的「大員第一王國—大肚王國」是多角色敘述的史詩,為平埔認同的內涵勾勒出重要的輪廓。詩人透過大肚王(歷史所記載的Quataong)的口吻這麼寫著:
真濟台灣人規世人攏咧拜地基主/公也拜嬤也拜/父也拜母也拜/囝也拜孫也拜/年頭拜到年尾/四季攏咧拜/但是攏毋知所拜的地基主/是啥人?/台灣上早開墾的地基主/無人講會出伊的名/少數叫會出名姓的/即是我!/恁拜的即是我!Quataong
這一段宣告就是詩人所要提出的平埔史觀的中心:大多數台灣人都是平埔後代,只是不自知而已,台灣人徒有敬拜地基主的習俗,卻不知敬拜的對像其實就是平埔的先祖。大肚王的角色是典型的提喻(synecdoche),他代表著所有被台灣人遺忘的平埔祖先。接著,從平埔族大肚王國的生滅,我們的想像進一步落實在具體的部族史實上,它透露出平埔族群已經初步實現了政治制度的統治芻型,這,似乎又是歷來的統治者想要掩蓋的──例如漢人的外來統治政權總是宣稱他們對於台灣的統治是與天俱來的──大肚王國的存在,也就扯破了外來統治者歷來的瞞天大謊。簡單講,在這章史詩的背後,我們看見了平埔自治的政治實體在歷史上的存在,僅就這一個代喻的安排,我們就可看出詩人在台灣史及平埔史觀上的獨到。另一方面,讀者在這一章所得到的額外禮物是,我們可以在333行的精塑過的詩句裡,極有效率地體認到這一段歷史,完整中不乏細節,詩人對於歷史敘述的簡裁與壓縮的功力高超。我們讀到像是這樣的詩句:
研究台灣歷史的學者/重新閱讀荷蘭檔案伸手掀彼領/披佇母土有身的大肚頂的絲紗巾/掀開當時村社茫霧的透早/竹抱葉尖的露水/祖靈長夜喘喟的珍珠/無數粒/粒粒攏落落公廨頂新鋪的稻草上
歷史的背景在晨霧與露珠中被描繪出來,在帶著感情的口吻中溶入了初生意象的清新,這本身就透露出平埔史觀的隱喻:在未被侵擾前,大肚王國的存在曾是何等美好。然而,這個美好的開始在經歷了荷蘭人的「金獅島討伐」、「華武壟討伐」及清國的「大甲西社事件」等外來的侵略之後,徹底被摧毀了。
大甲西社從此被迫改名為德化社/事件結束後參予抗清的「番社」攏被滅村/各族人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里一帶/清廷用賞燻賜布「以番制番」的手段/引出大肚王過去捌統轄過的岸裡社攻打大肚番王族裔/番王族群勢力完全衰退/大肚王國最後瓦解滅亡
從這一章我們看見了外來統治的殘暴以及族群的自我在高壓下被分化的悲哀,這一段史詩引出族群認同的重要課題:我們的自我圖像,該如何在高壓及侵略者的刀槍鐵蹄下堅定固守?
在「雨落佇咱查某祖的腹肚頂」,詩人延續了這個問題的闡述:
漢人滿州人位大陸看大員/是偏遠邊界外的鼻屎幼仔/荷蘭人位遙遠廣闊的大海看島嶼/是偎岸喬買賣的新天地/海權佮陸權交戰下的台窩灣
從漢人的眼光看台灣,台灣是偏遠化外之地,從西方荷蘭人的眼裡看台灣,台灣是和日本人、漢人、台灣人做生意的跳板,對外來者而言,台灣只是經濟資源,他們想的都是如何控制台灣人(原住民):
麻豆酋長企圖偷渡去日本/普特曼斯徵調麻豆酋長任遠征軍隊長來控制伊/調派新港社人去攻擊其他平埔社/若毋去攻擊一律上絞刑台處死/利用新港社的青壯年為荷蘭人賣命
漢人小結首用阿片薰予咱的查埔人吃/漢人大結首用縛跤布縛咱的查某人的跤
外來的統治者或者透過武力,或者在分化後利用部族之間的矛盾、結合其他部族的武力來對付台灣平埔族,先予威嚇懷柔,再利用土官結首施行統治,在部族內部進行抽稅與土地掠奪,導致:
荷蘭公司對Favorlang虎尾壠社眾/規定每戶愛繳納稻仔十束及鹿皮五張/平埔人打鹿/愛申請荷蘭公司許可執照/公司賤價收買鹿皮鹿肉/剝鹿皮運銷日本/鹿肉曝脯運銷中國/交換木材衫褲
鹿骨予人焢膠/陶鍋內阿立祖靈嗞嗞噗噗/滋補所有侵佔者/精血氣神的橫暴
這些詩句寫盡了平埔族的慘狀,鹿皮、鹿肉、鹿骨除了代表台灣被剝削的經濟物產,它們同時也象徵了平埔本身的遭遇,在生命與經濟被掠奪之後,阿立祖靈嗞嗞噗噗,悲慘的意象讓人震慄。這些震慄的歷史意象,促使了詩人在意識的最底層與平埔族的祖靈對話:
阿立祖換青了後/規瞑攏落袂停的雨/雨滴聲叮叮咚咚/落響佇咱查某祖的腹肚頂
台灣的母土在此昇華,成為母性的阿立祖(查某祖)的腹肚,整夜下不停的「雨」,既象徵了不曾停歇的、落在這土地上的悲慘命運(雨的意象,在神話理論裡總是和洪水的意象有關);但另一方面,因為「換青」一詞蘊含了水所代表的更新(神話理論裡的復活),連結在這裡的雨水,也就同時象徵了對於新命運的期待。在悲慘與期待復活的複雜情緒中,詩人甦醒過來,但他發現台灣人像是沉睡的一群人,「規陣攏佇生活中/慢慢自殺」,唯有清楚身世的詩人,在暗夜中歌頌著:
西拉雅/妳是干戈盡出/血緣融合的後代/頭毛長長流動/黑波轉踅的河水/鼻樑留著/山脈原始的挺秀/身軀肩頭懸佻/深山松梧的翠蓊/眉頭目睭不時咧編織/晚春上迷醉的漁網
我們很難找到比這一段及其前後更美麗溫柔的西拉雅書寫,母性的西拉雅形象和土地的形象完美地融成一體,讓人嚮往。這個形象同時暗喻了台灣人的女性先祖和台灣的土地,不僅美麗,且多面豐富:
妳面容的天色/閃雷中/變幻陣陣莿桐花的紅/七里香的白
草帽仔底的面容/面紗披過的夏日/笑聲的陽光/佇嘴唇上的花講恬靜的言語
如此,在詩裡,我們彷彿和阿立祖面對面相遇,但也在這一章的結尾,我們回到了現實:
歕出來的燻煙散了後/遮已經是漢人的城鎮/西拉雅/妳到底落入佗一個門第?
在這裡,西拉雅的意象,歸結為隱藏在漢人面目背後那一層說不出真正身世的悲劇,而這個身世的悲劇,和台灣之所以是「累世之靶」,可說是緊緊相依的。在如靶的受難史中失去族群自我,為了生存必須放棄身份,甚至不得不認賊作父,這就是過去平埔命運的寫照,也是關於台灣人命運最重要的隱喻。在詩人的眼光中,若要抵拒這個命運,唯有藉著「累世之靶」一章所提及的「反」,從對命運的反抗中歸回Sanasai的純真。
5 二個美學特點
在探討《累世之靶》的歷史和族群意涵的同時,我們可以進一步深究這首詩的美學特點,這裡,我先舉出其中二個要點來和讀者分享。
5.1 象徵美學
這首詩的美學特點,首先最顯著者ㄨ特點ㄧㄢ事ㄢ,就是象徵形象的建立。就現代文學的技術面而言,形象的建立是重要的一環,詩人透過形象傳達情感和思想,也藉形象來進行象徵或者隱喻。本詩的作者在這麼長的詩作裡描繪了許多形象,我們要特別注意,在這些形象背後他所象徵的對象,許多時候和族群的存在主體有關。例如前面提及的「鹿」的象徵形象,就是成功的典型。因為殖民者的經濟需求而被大量獵捕的「鹿」,象徵了被剝削的平埔族和祖靈,也象徵了更廣泛的台灣人受外來經濟殖民的歷史。
一六二五年中國一百隻戎克船駛來Tayouan採購鹿肉/鹿肉傷濟公司將鹿脯做軍糧/鹿骨漢人雕刻器材/鹿角煎熬成膠/鹿舌、鹿鞭、鹿筋做中國的壯陽藥
鹿骨予人焢膠/陶鍋內阿立祖靈嗞嗞噗噗/滋補所有侵佔者/精血氣神的橫暴
鹿肉予人曝乾/牽手的腱肌變脯/痛苦懸懸藏佇博物館是/真少人讀有的新港文書
鹿鞭予人浸泡/藥酒發作漢人上愛的壯陽史/敗腎心虛掩崁/洩精佇平埔查某祖腹肚頂的痕跡
詩人不只寫泛寫「鹿」,而是精細地把鹿的軀體部位進行即物主義式的描寫,賦予其作為「鹿」(即象徵作為「台灣人」)的存在意涵:以「鹿」為被壓迫、剝削的存在主體,鹿骨隱喻了平埔的阿立祖,在陶鍋中滋補了傾略者的暴戾嗜血,如此,「鹿骨」和「啃鹿骨者」的對立,就是「平埔台灣人」和「掠奪平埔台灣人的侵略者」的對立;鹿肉被曬成乾,痛苦的哀號也曬乾了,鹿肉充實了侵略者的軍糧,在歷史裡變成了無聲的新港文書;鹿鞭被浸泡,用來掩蓋逞慾者的心虛無能卻又巨大無比的慾望,在這個侵略者巨大的慾望之下,鹿所象徵的平埔人也就逐漸地被害沉淪。上述段落的文字,我們可以看見被害者的臉孔彷彿因痛苦而扭曲,甚至帶著表現主義式的吶喊抗議。
又比如第九章中描寫國史館的檔案室:
國史館的檔案室/冷氣冷到親像殯儀館/冷凍死人的冷凍櫃
光到反黑的/走廊/正爿檔案室典藏/「蔣總統史料」/左爿檔案室典藏/「二二八事件田野調查資料」
受難者歸群擠一間/加害者一個人佔一間/攏恬恬倒佇冷凍櫃/對相的歷史/敢擱會講話?
國史館的檔案室,無疑象徵了權力所介入的歷史詮釋的荒謬性:加害者一個人佔據了一間,相對於二二八受難者一大群擠在同一間,雖說其荒謬,卻又突顯出受迫害歷史的真實感,整段描寫從溫度(冷氣)到光線(光到反黑)到處境的鋪排,可說是成功的形象營造。詩人同時也藉由死亡的意象訕笑了威權者不能獨免於一死的虛妄性。
另外,詩人也擅長於使用轉化的技巧,在台灣人生活的物質中找尋精神象徵,例如第十章的這一段詩句:
鹽是咱民族久長被曝的結晶/苦是鹽的根源 苦是鹽的底柢/鹹是咱的命/醯今年按算明年的吃食/醯頂代的屈辱映望後代的出頭/鹽是民族留過血汗的種籽/種籽發分杈的樟樹/樹椏大小支手骨/隨在人斬/隨在人剉/隨在人榨/隨在人煉/甲污暗剝削提煉做潔白的樟腦/無見血甲咱頭殼心的白腦髓抽出來/永遠甲咱當作縮乾的焦粕擲捨/出賣咱憨直的潔白/換做帝國貪腐的紋銀
鹽是海水長年被曝曬的結晶,詩人把這個特質轉化為民族精神的結晶:長年被曝曬後的鹽,雖有苦的根源、苦的底蘊,但我們都需要依靠鹽的鹹味生存。鹽裡本身就有象徵,延伸到「醯sīnn」(即鹽漬)的動作也是台灣人的生活智慧,讓食物可以存放到來年,詩人將這個鹽漬的動作進行轉化,成為對民族屈辱的耐受承擔,以寄望民族下一代的出頭。接著,台灣另一樣重要物產樟樹在這裡也轉化成了台灣人生存的象徵。樟樹在台灣隨處可見,樟樹可以粹取出樟腦,台灣的樟腦產量一度是世界之冠。為了粹煉樟腦,樟樹的枝幹被砍斷,被榨被煉,白色的樟腦就好像是樟樹的腦髄,而腦髄意味著台灣人的精神、記憶,一旦被榨乾,剩下的渣粕就像是沒有靈魂的東西必須要丟棄,這就象徵了台灣人若缺乏主體性與自主性的危機。
藉由對台灣常見物種進行即物式的象徵描寫,這種運用形象進行象徵的技巧,來到第13章的「鹽佮糖」,變成了更大篇幅的思想辯證。
收割過累世人數千萬枝的甘蔗/但是自來毋捌收割過甜蜜/收成過累世人數千萬擔的白鹽/但是自來毋捌收成過輕考
鹽業和糖業的發展本身就是台灣人長年受經濟剝削的表徵。蔗農幾代下來,收割過千萬枝的甘蔗,但是從來沒有收割過甜蜜,這樣的詩句道盡了奴隸般的辛酸。鹽和糖不只具有經濟剝削的表徵,詩人也發掘出糖和鹽中的精神象徵:
鹽和糖/台灣人民苦樂的元素佮象徵//鹹和甜的濟少/指標台灣文化
講起失敗者的因原/歸尾是手段行止傷鹹/鹽下傷濟/欠缺人和致使眾叛親離//見風轉帆隨勢搖旗/依附 (Dead bird, oil painting, by Ryder, Albert Pinkham, c 1879) 罪顏雪花─罪
伊有罪
伊看起來就是有罪的型
壞看、骯髒、穿ka破爛爛
佇樹林中,伊hon發現和伊(她)的屍體做伙
厝邊說,伊恬恬seng死pon鼠、臭頭爛耳的狗ah
ke有死蛇
伊說,遮是伊唯一會當接近的物件
“你看我!“ 老人用平靜單純的口氣講話
“我家己de是一個死物
已經真困難由死亡ka我帶來屈辱,
狗仔死佇路li,鳥仔ka蚼蟻食伊的目睭,
就算一隻死ah足壞看的niao鼠ma有隱私
我清除伊面上的油垢,身驅頂的血跡
我幫伊梳頭,睏佇她的邊ah
睏佇伊的跤下兩日,我的狗仔ma相仝按呢做
我幫伊穿我會當揣到上好的衫仔
伊看起來足慘,親像擲sai佇草堆裡的糞埽”
無人關心,du du ah好伊(他)替伊(她)做這項代誌
“我續落去想,伊愛按呢一個人偌久?
我知影警察會來翕相
Ka伊無穿杉的相登佇報紙
每一個人le吃早頓的時陣,目睭金金看伊
我,只是ho伊的靈魂有夠時間去安頓 “
罪
他有罪
他看起來就是有罪的樣子
醜陋、骯髒、穿著破爛
在樹林中,他被發現與她的屍體一起
鄰居說,他常玩弄死松鼠、皮破肉綻的狗
還有死蛇
他說,這些是他唯一能接近的東西
“看著我!“ 老人以平靜單純的語調說著
“我自己就是個死物,
已很難由死亡帶來羞辱,
狗死在路上,鳥與螞蟻啄食它的眼睛,
即使一隻不雅的死老鼠也有隱私
我清除她臉上的污垢,身上的血跡
我幫她梳頭髮,睡在她身旁
睡在她腳下兩天,我的狗也這麼做
我幫她穿上我所能找到最好的衣服
她看來很糟,像丟在草堆裡的垃圾”
無人關心,而正好他為她做了這些事
“我繼而想,她要如此一個人多久?
我知道警察會來拍照
將她的裸照登在報紙上
人們吃早餐時注視著她
我,只是讓她的靈魂有足夠的時間去安頓 “
Guilt
Guilty
He just looked like guilty
Ugly, dirty, wore in rags
He was found with her body in the woods
Neighbors said he often played dead squirrel, wounded dogs
And dead snake
He said these were the only things he can be closed
"Look at me!"the old man spoke in a calm and simple tone
"I myself is a dead thing,
It’s difficult to bring about shame of the death
The dog died on the road, birds and ants peck its eyes,
Even an indecent dead rat has the privacy
I cleaned the dirt on her face, bloodstain on the body
I helped her comb, slept by her side
Slept at her feet two days, same as my dog
I helped her put on the clothes I could find the best
She looks awful, like the rubbish thrown in the haystack "
No body cares about it, but just that he did these things for her
"I then thought, how long she should be in this way?
I know the police will come to take pictures
The nude photos of her will be on the newspapers
People stare at her at breakfast
I just let her soul have enough time to settle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