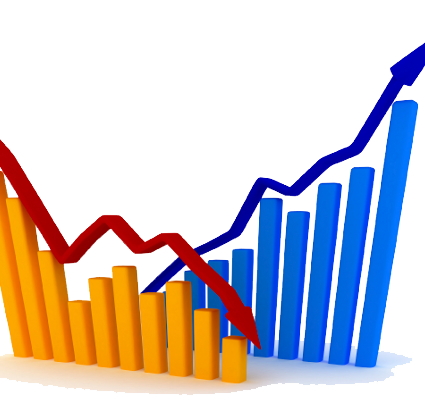以善意回應霸凌,可以嗎?(上)
◎史英 / 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幾個人圍了上來,老大在最中間,右手裡的鉛筆敲著左手心,一面笑著,但並不說話;她死命盯著那支鉛筆,只有一個念頭:它就要扎到我身上來了,心裡非常害怕。這個時候,也不知是哪來的靈感,她突然聽見自已開口說:我想跟你做朋友…」
假定這就是某個校園霸凌的一個場景的可能的開頭,做為關心小孩的父母或師長,看到「做朋友」三個字,我們會有什麼感想?
有一種感想是心酸:傻孩子,你怎麼會笨到以為人家肯跟你做朋友?接著會覺得生氣:是哪個二百五教你友善校園的?確實的,平常學校裡教的那一套,什麼相親相愛,互相尊重,朋友有信(別忘了上一句就是長幼有序,正是大欺小的好理由),對於生活在真實「人間」的我們的小孩,實在是—不知怎麼形容,且用一個比喻—莒光日(註一)的標準教材!
那麼,對於如何因應「被圍」的情況,我們可以怎麼教小孩?教他跑,但現場顯然是跑不掉;教他告老師,但老師顯然不在場;教他大聲呼救,這似乎是一個辦法,但也要聽到的人肯管這個閒事,而且可能造成以後的日子更難過;所以,應該教他必須忍耐,保持冷靜,不要「刺激對方」(還記得我們對中國的政策嗎?),以便—實在想不出接下去可以「以便」怎樣,且引用總統的指示(註二)—以便讓教官(註三)「主動發掘」、讓老師「配合偵辦」吧!
本文的目的並不在批評當局,前段只是為了請讀者了解,小孩需要實質的幫助;這個需要是如此真實,絕不可以用政治口號和官樣文章去唬弄。我們認為,教導小孩如何面對「橫逆之來」,除了同學,也包括如何面對「不講理」的師長,乃至不合理的教育制度等等,絕對應該是教育中的重大議題;然而,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是我們成人在生活上,隨手舉個例子,例如生病的時候被某個醫師的無理態度所「霸凌」,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
這並不奇怪,我們所受的教育,只告訴我們事情應該怎樣,卻從不說如果事實並非那樣你可以怎樣。所以,在教育中發展這個新課題,也就是教小孩如何面對霸凌,包括著面對師長或制度的霸凌,就變成我們無可逃避的責任。這當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須要深刻地思考,也須要實質的研究,但我們更相信,須要先從實際的、具體的、小小的問題開始。
現在,就讓我們回到一開始所提出的場景。
一、善意不等於求饒,求饒並不是善意。
本文一開始的那個場景,讓我們對所謂「善意」產生極大的懷疑;這就是「具體情境」的價值:若是只用抽象的語言來談論,很容易就冒出類似「好心買好心」,「不打笑臉人」,「善意化解敵意」這一類的話;但透過具體畫面來想像,很容易就發現這些話其實非常不著邊際,如果拿來教導小孩,小孩下一回大概就不會再來求救了。
然而,具體情境也有陷阱:若是不能透視背後的真實,只看表面的假象,往往會把事情想左了。這個場景裡的真實是,「想做朋友」這一句話可以有非常分歧的意涵:它可以代表求饒,但也可以代表善意;前者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從困境中得到釋放),後者是為了對方的利益(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善」),這兩者在本質上並非等同。
「做朋友」到底是求饒還是善意?其實要視對方的解讀而定,而這個解讀又決定於己方的神情和心態(詳見後文)。如果一旦被解讀為求饒了,在往下的發展中,通常不會得到「饒恕」;因為霸凌者心中所想的,是要給受者一個「懲罰」,就像別人向來給他各種懲罰那樣,而顯然沒有一種懲罰是「做朋友」。換言之,如果是求饒,必須換成另一句話,例如,「我想做你們的手下」:既是「求」別人,理當提出某項交換,而那個交換條件,就是你該得的懲罰了。
所以,在教導小孩如何面對霸凌的時候,我們必須謹慎,不宜讓小孩誤以為我們要他求饒;求饒未必能夠成功,而成功的代價未必是他能付得起的。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明白,並不是「善意」讓人覺得心酸甚至憤怒(如前文所述),而是那種低聲下氣的「求饒」;事實是,在求饒中根本沒有什麼善意,只有想要逃脫的私意而已(而這一點正為對方所深知)。所以,我們還不能驟下判斷,以為善意在面對霸凌時完全不可行—一般人以為善意無用,其實是把求饒誤為善意了。
二、把人妖魔化,杜絕了防患未然的機會。
讓我們再回到現場,接續前面的故事:「…開口說:我想跟你做朋友。老大楞了一下,沒有料到這一招;但他的反應很快:那我們就來談條件。她也很意外,從來沒想過做朋友還有講條件的,只能呆在那兒不說話;而老大的嘍囉們,也一改原先看好戲的表情,露出了好奇的神色。不過,老大還是老大,僵局終於要靠他來打破;他緩緩伸出一隻腳,低沉著嗓音:做朋友的條件就是,你來舔我的腳趾頭!」
有人要跳起來了:看吧,我早就告訴你善意行不通,善意只能自取其辱;但本文的讀者應該不會太吃驚,正如前段所預料,老大把善意誤解為求饒了:既然求饒,那就再出更難的題目讓你來求。話是這麼說,但我們還是不能接受:怎麼可以這樣?他可以說「我要你當手下」;不過,這樣理性而又文雅地講條件,是像作者這樣理路清晰的人寫在文章裡的,實際去做怕都很難,如何能期待於一個孩子,或少年?更何況,「舔趾」也不是一般人輕易想得出來的花樣;應該是另有所本:或者在電影或漫畫裡看過,要不就是有過相關的類似經歷,不然,也許他很認真看新聞,仔細研究過舔耳案(註四)?
提到那個「案」,當然只是為了博君一笑;博君一笑,卻是為了請大家不要太早生氣,以便繼續閱讀本文。我們有一種習慣,對於不了解的人,很容易將其妖魔化;把對方想像成一個惡魔,任由它把自己嚇得半死,再沉溺於恐慌,享受自憐或義憤,並拒絕思考。當然,如果事情已經發展到嚴重的地步,例如當霸凌者犯下刑事罪,我們可以理解有些人不願意去理解;但在這之前,我們就堅持,任何人都應該用心去體會施霸者的背景,例如想想他怎麼會說那種話,才能了解事情的原委和真相。
最重要的真相是,任何嚴重的事情,都有一個沒那麼嚴重的開端。我們要教導小孩的,應該是防患於未然;但妖魔化的思維模式,卻是跳過開端,直接在心裡把事情推到最後,因而就把所有正面的可能性都排除了,也不可能為善意留下任何空間。當然,如果我們現在談論的是希特勒或其化身,也許另當別論;但我們正在談論一個小孩或少年,他就算非常之壞,到底能壞到怎樣的地步?如果我們還期待他多多少少能放受害者一馬,我們總要相信他至少有一點點的「好」,否則,被霸凌就等於被兇手判了死刑,還有什麼討論的餘地?
所以,就因應霸凌而言,妖魔化才是真正的死敵,尤其在教導小孩的時候:絕不能讓小孩把對方視為萬惡的仇敵,不然,就杜絕了所有解決問題的機會。
讀者會說:這些都還是抽象的言詞,我們想知道是,那個「她」接下來可以怎麼辦;那麼,讓我們再回到具體的場景。
三、唯有真誠的善意,可以開啟無限的可能。
接續前面的故事:「…條件就是,你來舔我的腳趾頭。沒有人想得到,針對這個極具攻擊性的要求,她反而知道怎麼回答了;其實這也有跡可循,老大撂下的狠話,在無意間把事情帶到了她所熟悉的領域,那就是,關於朋友。關於朋友之為朋友,以及怎樣才能做為朋友,她曾經想過很多;所以在那個當下,她就說:我是要跟你做朋友,並不要舔你的腳趾頭—沒有朋友是舔腳趾頭的,舔腳指頭就不是朋友了!」*
(編按:一個小女孩,為什麼能用這種方式回應對方的羞辱,說出這些大人也未必能說出來的話?聽到她這麼說,老大會走上去給她一個耳光嗎?接下去,她又能怎麼反應?故事到底會發展到什麼地步?還有最重要的,我們到底該如何教小孩因應霸凌?因為本文篇幅太長,我們只能留在下一期的本刊中再為您披露。情非得已,敬請原諒,並請熱切期待。)
.......................................................................................................
註一︰在國軍部隊中,每週訂有一日不出操,只上課,是為莒光日。
註二︰馬總統針對校園霸凌指示:主動發掘,明快處置,配合偵辦,對外說明;這個指示同時也出現在教育部「防制霸凌專區」網頁的入口(另外,在二○○六年北市長任內對政風人員講話,以及二○一一年塑化劑風暴對媒體發言時,也用過同樣的十六個字箴言,一字未改。)
註三︰教育部把霸凌業務劃歸軍訓處,而所有校園霸凌的通報,也是要通報到上級的軍訓單位。
註四︰舔趾當然也可能是「跨下之辱」的一個衍伸,但依照一般觀念,這種孩子應該不會想起韓信的典故,還是讓他記得李慶安比較像一點。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