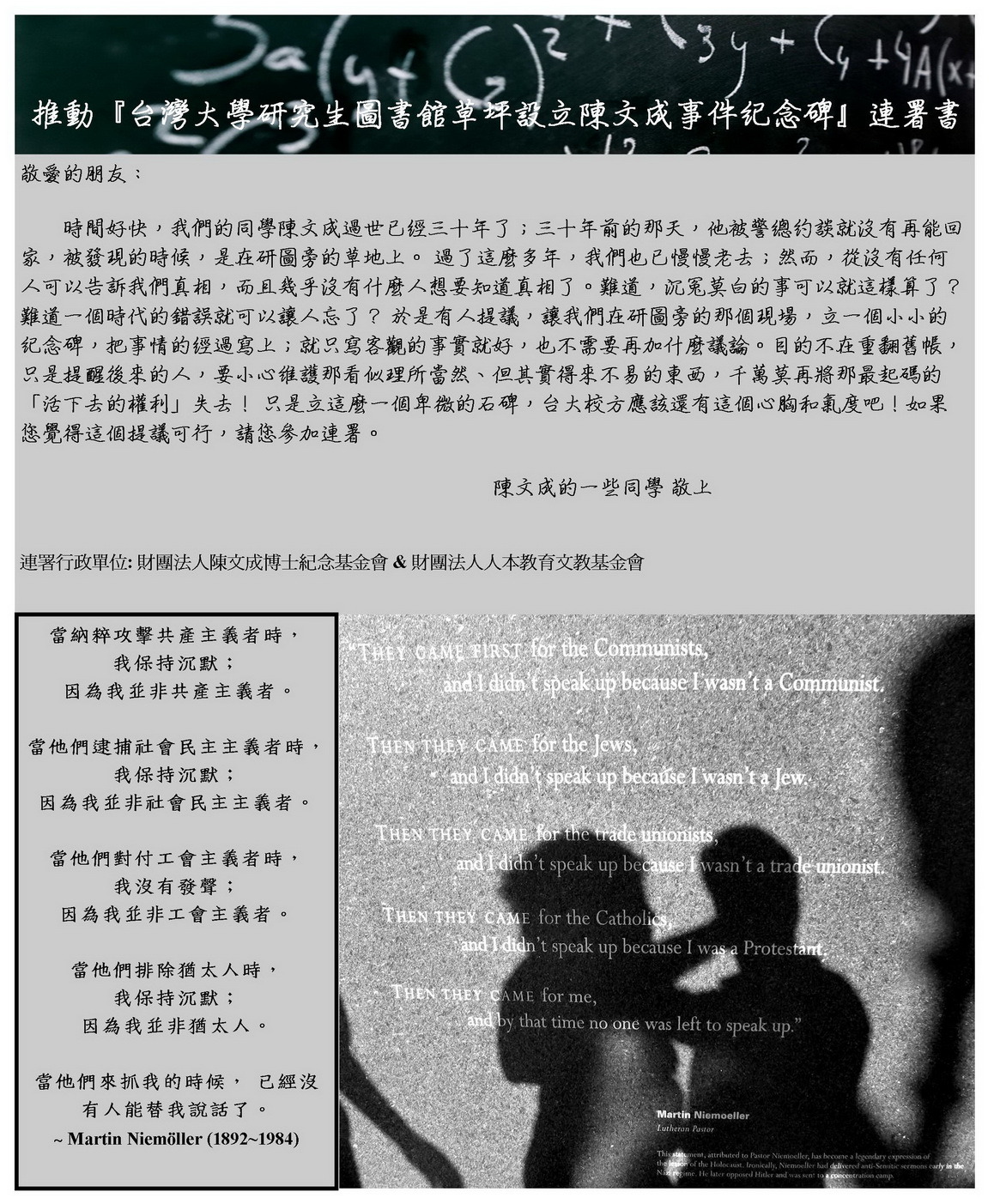【人本】重拾「教鞭」就能解決霸凌?─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ly 30,2019重拾「教鞭」就能解決霸凌?
◎馮喬蘭(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恢復體罰制度是處理校園霸凌亂象的有效方法嗎?也許在做出補救措施之前,應設法釐清真正的問題所在。
對付霸凌只能靠體罰?
一連串的動作,讓台灣社會似乎進入一種全民總動員的緊張狀態。教育部長天天宣示要對抗霸凌,像在抗煞(或抗H1N1);內政部長也趕緊加入戰局,出動警力、加強巡邏;教育部更派軍訓處負責反霸凌,動不動便說隔離,嚇倒許多人。「霸凌」宛如人人恐懼防範的病毒或是社會之瘤,而在媒體對種種事件的報導裡,這些校園霸凌的滋事學生更淪為「社會的罪人」,彷彿霸凌這件事只剩下「小孩子無法無天、欠缺管教」這樣簡單不過的意義。
一部部小影片在媒體上播放,觀者被嚇呆了:我們的孩子怎麼會這樣?如此詆毀他人、拍裸照、蓋垃圾桶、拼命毆打,甚至連路過的人也來湊一腳。這些孩子邊打邊羞辱對方,有時還振振有理地說:誰叫他背叛!我們的孩子到底怎麼了?被這些畫面情景嚇到的社會大眾,將這些孩子視為「霸凌者」、「施暴者」。然而當這些名詞進入人心後,往往也是簡化論辨和窄化議題思考的開始。當人們視孩子為「霸凌者」,對孩子的恐懼便極易取代進一步的思考與疼惜,因此給予支持威權管理者恢復舊制的機會。於是許多校長趁此機會大喊:修正零體罰政策,給我們懲戒權!
以暴治暴的惡性循環
以懲戒取代教育,是誰可以得利?有些人以為,如果讓師長擁有多一點管教工具,如適度體罰或其他懲戒的方式,也許可以保護那些被霸凌的同學。但這樣的想法疏忽了過往的實證經驗校園一直以來都有體罰、罰站、記過、交互蹲跳等所謂各種「管教」的方式。在立法禁止體罰前,學校的霸凌事件還是層出不窮,而那些欺負同學的「霸凌者」,其實多半也被體罰過。一味處罰的結果,往往會讓大部分受到師長懲戒的學生,藉機去找弱者出氣、報復。
這是一種惡性循環——用負面手段要如何得到正面結果?去問那些被欺負過的孩子會不會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師長,得到的答案通常是不會,因為怕報告後下場會更慘。他們之所以害怕,就是擔心即使告訴大人,大人也不會處理好——特別是當大人只懂懲戒、不懂教育的時候。
2006年底,台灣通過禁止體罰的法案,但2010年的調查卻顯示仍有四成一的國中生被體罰過;要說是零體罰造成霸凌,實在缺乏立論的基礎——校園霸凌現象早在此法制定之前就時有所聞,更何況現在根本就不是零體罰的環境。可是,為什麼還有校長會將零體罰政策和霸凌牽扯在一起?這是因為他們不過是想要恢復體罰的制度環境,而非真的想解決霸凌問題。否則,怎麼會選擇一個已被證明無用的方法大肆疾呼呢?
教育者不應推卸責任
這種思維模式,其實是將霸凌發生的原因歸咎到學生的性格或其家庭問題;在將霸凌的責任歸咎到學生個人,讓學生自己面對懲處以求改過自新時,也回避了教育者應負起的責任。教育的功能本來在於協助學生面對問題,進而改變、啟發他的能力。假使教育變成了懲戒,只負責記大小過或處罰學生,那麼教育的專業又算什麼?想要恢復體罰制度的校長之所以令人害怕,是因為他們總想立威壓制,卻忘了教育真正的精神。
社會上對校園霸凌的憂慮應該要受到正視,但我們只看到教育界一再檢討別人、要別人負責。這些「別人」包括家庭、社會變遷、電影《艋舺》、網路、電玩和立法院……至於教育界該負的責任,似乎只剩下通報。可是「沒有通報要記過」、「加強通報頻率」等這些由教育部提出來的對策,怎麼看起來都像是推卸教育的責任呢?
從瞭解與接納做起
如果只從大人自己的利益需求來思考,絕對無法處理好霸凌問題;主事者必須去理解孩子的思維、生活狀況和需要。過去處理校園暴力的經驗顯示,那些讓師長頭痛的孩子,內心往往存著不安、脆弱和強烈的自卑感與罪惡感,在自我防衛機轉的運作下,表現在外便成了猖狂的態度,甚至是暴力攻擊。
該如何幫助這些孩子?瞭解與接納,是讓他們解除防衛的第一步,如此便可以協助孩子檢視自己的行為、覺察自己的情緒,進一步調整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改變生存的模式。之後我們慢慢會發現,這些孩子的霸凌行為,也許都是所謂的「反擊型霸凌」,因為他們都被升學壓力與威權管理狠狠地霸凌過。
光靠目前學校的能力與人力,恐怕無法應付眼前的霸凌亂象。教育部應該立即設立處理機制,讓跨領域的專業團隊形成校園支援系統,並結合社區資源,和學校一起用積極的教育與輔導來解決相關困境。霸凌是教育出問題的嚴重症狀,必須用教育的方式來解決。
◎本文原載于2011年2月號《人籟論辨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