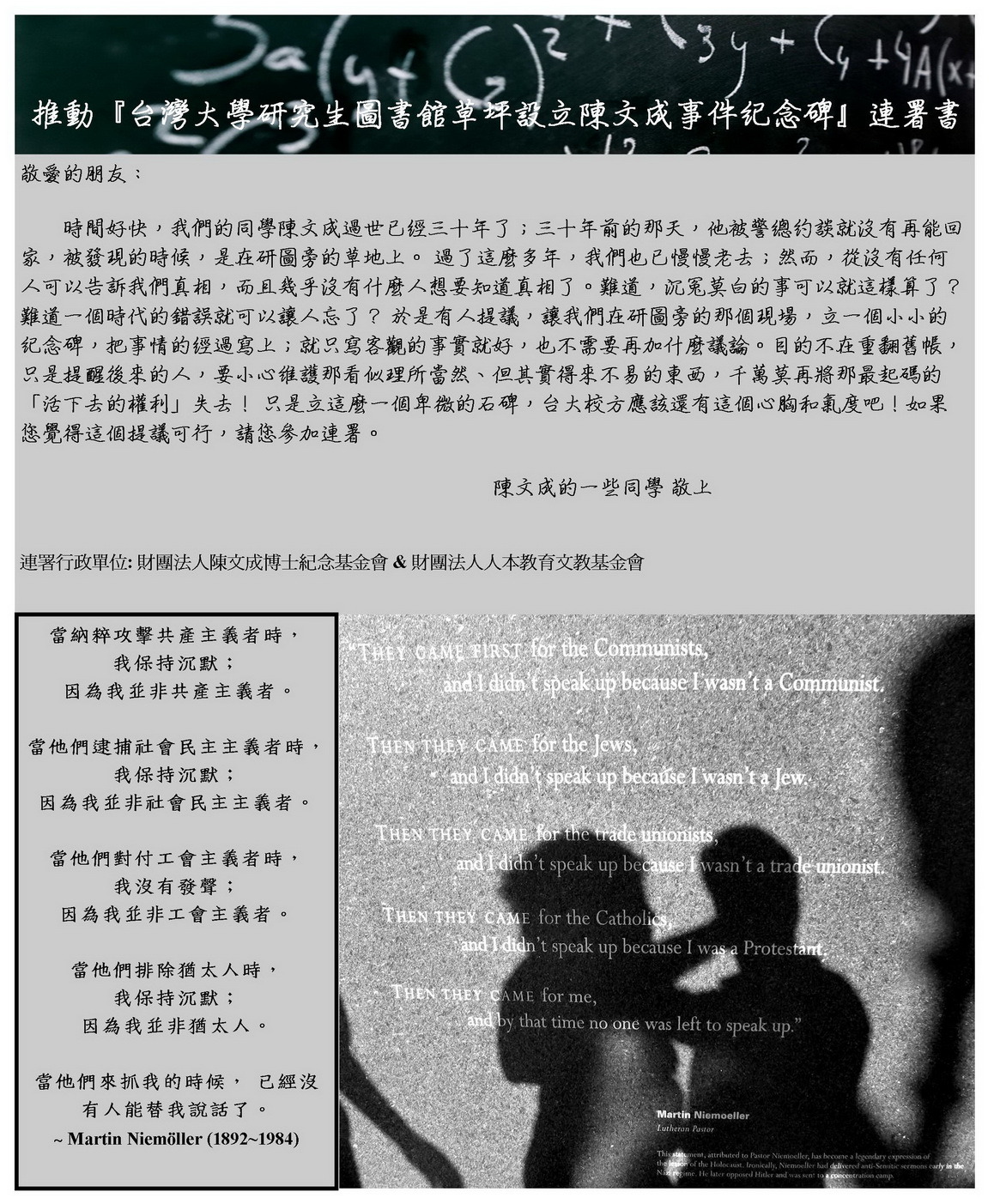春季「森林小學師資培訓課程」
我們在落實這種教育
讓好奇的眼光閃動,探索視界的興致勇於奔馳;
讓多元的思維論戰,追求真理的熱忱難以遏止;
讓求變的念頭勃發,翻轉心思追求有意思的生活!
我們在號召與眾不同的人!
2012春季森林小學師資培訓
將於3月21日開課
邀您一同翻轉視界,釀造好教育!
詳細課程表及訊息請參見BLOG:http://hef1987.pixnet.net/blog/post/28332691

2012.03.16人本教育基金會新聞稿
校園性侵,國家有責!
特教學校性侵案,教育部責任未了
一、背景經過
南部某特教學校自去年9月被揭露爆發一百多起駭人聽聞的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後,輿論譁然,前教育部長吳清基在壓力下不得不撤換校長。去年底公佈的懲處結果,從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以降,到前後任校長、主任等教職員等共計30人,各被處以大過一次到申誡不等之處分。
二、應作為而不作為,國家當然有責任
這所特教學校長年管理不善、隱匿吃案,對於孩子的求助置之不理;該做的性教育及情感教育、宿舍管理、校園安全規劃、通報輔導等等,都沒有做,從教育部懲處事由包括:督導不周、處理不當、工作不力、貽誤公務、未妥善處理疑似性平事件、未維護校園安全環境、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未依規定通報、延遲通報、有失管理責任、企圖隱匿事證、忽略學生求助訊息等等,都可看出端倪。
依據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特教學校如此嚴重的違法失職事件,除了監察院應該積極追究行政責任外,政府更應該主動負起國家賠償責任!
三、受害學生家長已於一月底提出國家賠償申請
目前有五個受害學生家長提出國賠申請(附件一國賠請求書)。這些孩子受害內容包括在校車上多次遭猥褻、性侵;在宿舍、活動中心遭性侵;從被性侵到性侵他人;等,另外還有『受害內容』如下
1.曾向大人發訊求救,未被理會:
包括隨車管理員、生活輔導員、導師、宿舍管理員、等,無論是當場得知或事後接到投訴,這些大人沒有作為,沒有處理,而有直接拒絕者(叫小孩回去坐好,不要管)。雖然做出性侵行為的不是這些大人,然而他們的忽視,卻造成孩子一再受害,當然有責任。
2.看過別人受害:
這是一個長期扭曲的環境。有人被侵害,有人侵害人,但都沒有得到適切的處理與輔導,演變成,看過的或被侵害過的,還轉為侵害者,而孩子們也只好變成「見怪不怪」。受害的不只是身體,還有心智!大人不思改變環境,每一個來到這裡的人都受到扭曲。
3.性平調查展開後,還在發生狀況
出事後學校只會裝監視器,並說:「那是孩子在玩」、「那是人的本性」。這種『只將責任放在小孩,矛頭卻不指向學校』的思維模式,導致學校不思積極作為,甚而還輕忽,讓侵害過A生的B生,與A生同寢室,未做任何防護安排。當事情再發生時,只會將小孩退宿,而不是改變措施,提供教育。
當家長質疑學校宿舍管理有問題,主任卻說:「學校不能保證學生的安全」,甚至建議改成通勤,完全忘了,小孩被性侵,學校有責任。我們必須提出國家賠償申請,要求國家負起責任。
四、特教學校性侵案,教育部責任未了!國賠不僅是要為過去負責,更為了保障特教生的未來
在法扶基金會的訴訟扶助下,受害學生家長提出國家賠償請求,希望能稍稍還孩子一個公道,並促使教育部正視特教學生的受教品質。然而從1月底送件迄今,學校未曾答覆任何賠償金額,也未通知代理律師等人展開正式協議,並打算以「會繼續給予受害學生心理諮商、保障就學就業」的說法施壓家長,促其撤回國賠請求。
五位提出國家賠償申請的受害學生家長,他們的心情就跟多年前為遭性侵的女兒要求國家賠償的媽媽一樣:「提國家賠償並不是為了要錢,就算給我一千萬,我也不願意女兒被性侵;提國家賠償是希望以後所有的特教生都能受到政府的重視,不要因為他們是弱勢者,就輕易被犧牲了。」。這位媽媽,花了4年時間走國家賠償訴訟。難道,這一回還要受害學生及家長受這樣的苦嗎?還是說,國家一定要將自己與受害人民對立起來,卻不能直接承擔責任,協議國賠呢?
根據國家賠償法(註1),賠償義務機關在請求提出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受害家長可提賠償訴訟,但我們極不願意採取此途徑,除了不忍受苦延長外,還是對教育機構懷抱著期許。如果教育部可以明白自己的責任,不漠視特教生的需要,並對於改善特教環境有意識,那麼理當承擔起國賠責任,責成學校儘快提出協議。
所以,我們要求教育部儘快開始協議!
註1.國家賠償法第11條
我在森小,思考活著的意義。
◎李依真
‧森小第十一期畢業生
‧目前為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碩士生,研究哲學、歷史認識論。
森小開啟我的哲思之門
在森小的畢業生中,我應該已經算是老牌了。現在回憶起森小的生活,非常確定它的豐富多彩絕不遜色於大學,事實上,它的多元性甚至勝於大學,而年幼的孩子則在這樣開放的空間中,被允許探索與自己性向吻合的道路。我大概是眾多例子中的一個,正好屬於被開啟了哲學思維之門的那一類吧!
目前,我人在日本,有交流協會的獎學金為後援,就讀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所,在日本哲學健將高橋哲哉教授之下,學習當代思潮與歷史認識論。二○○九年,在我來到東京之前,曾在人本募款餐會上見到了許久不見的朱朱與史英,當時史英問我:「最近還有寫小說嗎?」滿腦子都還停留在剛寫好的研究報告上的我,唐突冒出一句:「最近比較喜歡寫論文。」史英愣了一秒鐘,回答說:「算妳狠!」每次想起這件事,總是忍俊不住;史英大概不知道,即使畢業了那麼久,他的一句小小幽默或是不意之舉,總是一如往常地帶給我很大的勇氣。
森小帶著我,表述自己的感受。
我曾經是那種「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典型怪咖。正當其他森小同學盡情在球場、山坡上奔跑,以自己的身體輕快地接觸自然、享受自然的時候,我卻總是待在角落默默地想著「我幹嘛一定要活在世上?」這種想法也許對父母有些不敬,但是我就是對世界與自己的關係抱持著一種堅定的疑惑。
五年級,有一次我終於忍不住跑去問朱朱:「人為什麼要活著?」朱朱微笑地看著我,回答說:「這個問題問得很好,可是我沒有辦法直接回答妳。因為每個人的答案可能都不一樣,妳的答案也必須要自己去尋找。」我還記得那正是朱朱開始教授高年級作文課的學期,朱朱那種出其不意的教學,大概是使我有勇氣衝去問她這個問題的原因吧!朱朱的作文課,帶我們從身體感覺,例如味覺、聽覺、運動之中去體驗自我,並將感受性轉以語言,表達、敘述。
多年之後,我了解到這種訓練極其重要—如果人這種存在必須透過敘述行為,如果人本身就是一種敘述的動物,那麼重要的是,如何讓語言與生命經驗能相互通達,而非單方面地只能驅使空洞的陳腔濫調,或感情澎湃卻欠缺語言的思考。自從在作文課中盡情嘗試書寫之後,我漸漸學會使用語言圍塑我的情感,先圈出範圍,再進一步去推衍、逼近我的問題意識。
森小經驗,支持我尋找活著的答案。
可以特別提出來的一個例子,是朱朱曾經將課程分成三次,指導我們寫小說的經驗。當時我正在煩惱與同寢室同學的交際關係,於是便以「友誼」為題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在小說中,我描述了在小女孩的團體中存在著屬於她們的倫理規範,而被這種規範箝制住的孩子,會本能性地抑制自己的不悅與憤怒,但是她們仍然嘗試著從規範中逃脫。之後輾轉聽我母親說,讀到這篇小說的史英感動地掉下淚來,而這件事對我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促成我畢業之後仍持續提筆寫作的動機,並且一有新作就厚顏無恥地寄給史英—單方面地逼迫史英閱讀—於是導致他每次看到我就聯想到「小說」。
從小說到哲學,我並沒有走的太遠。同樣需要省察自我、並對自己的問題意識有所堅持。成長途中縱然有許多迷惑與岔路,雖然我也是一路哀哀叫,卻總是有信心堅持尋找自己能展現百分之百熱誠的道路。森小的經驗支持著我,活潑多元的感受性,至今仍然是我寫論文時最重要的參照點。回應朱朱當時的啟發,我仍舊耐心尋找我的答案。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7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