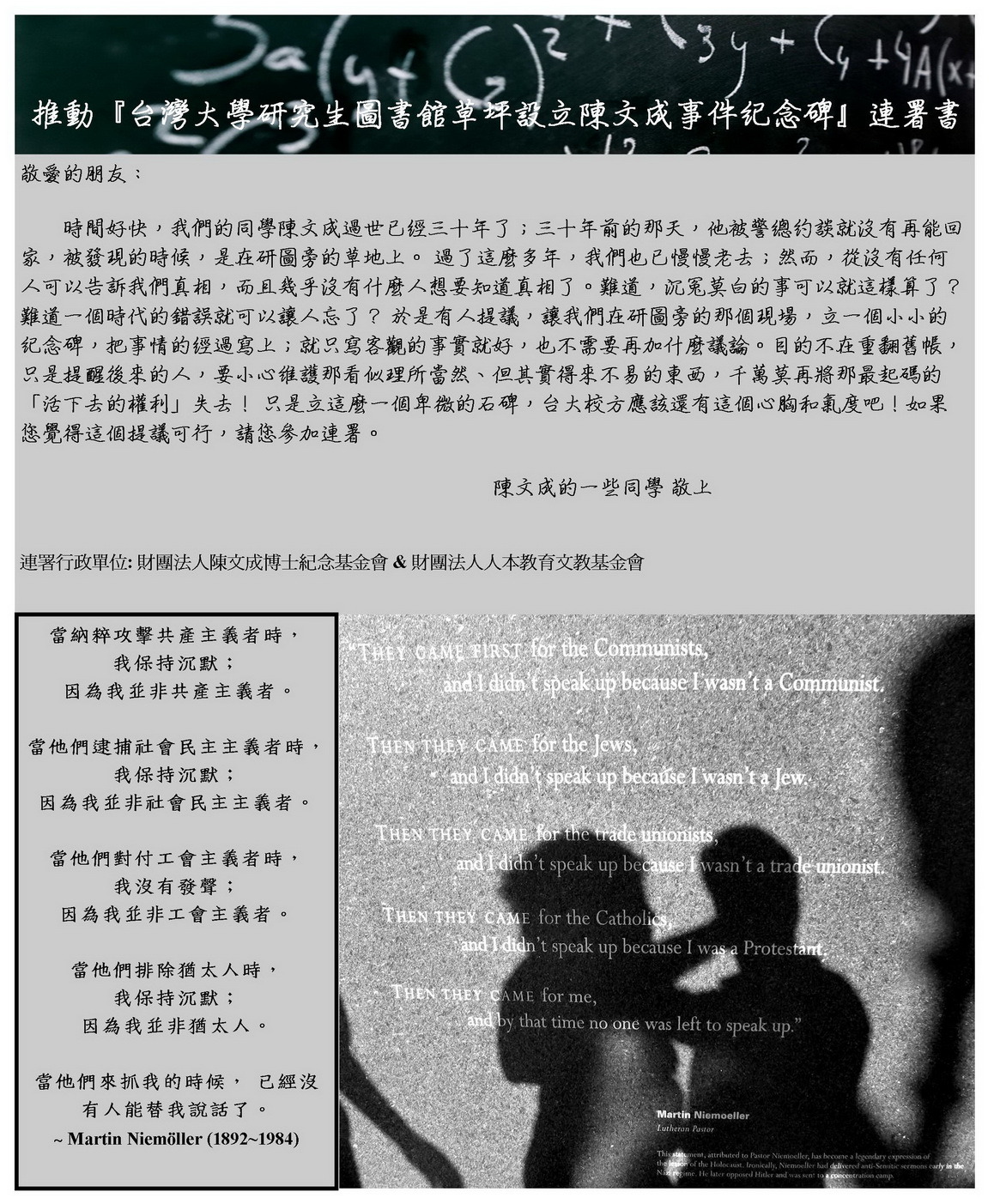【人本】從浪潮 The Wave 說起 (中)─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ly 30,2019從浪潮 The Wave 說起 (中)
◎史英/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在前期札記中,本文的上篇〈從浪潮說起(上)〉基本上談論了三件事:在「相關的學術研究」中,簡單介紹了二次戰後關於「人可以壞到什麼程度」的系列 研究,包括Asch的從眾實驗、Milgram的電擊實驗、Zimbardo的監獄實驗等;接續的「與相關研究的比較」,則闡述了Jones的浪潮實驗何 以比正規的學術研究更具啟發性;然後焦點轉向教育現場,在「那位Jones和那種教師的比較」中,討論了極端嚮往秩序的「那種教師」何以未能如Jones 那麼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此文下篇將進一步深討相關教育議題,最後再回到對於人類未來的關懷上。
…對於少數擁有那種能力的「那種教師」,也就是某些人心中的「power教師」,我們必須仔細分辨,不能僅僅因為他能讓學生心悅誠服,就一廂情願地 認定他是教師的典範,還得看他提供給學生的,是真知灼見呢?還是對他個人的崇拜;再者,我們也因而了解了,任何一場人類的浩劫,都需要一個英明領袖,這位 領袖害盡蒼生,但我們必須小心,他的英明,在他那個範圍裡,並不是假的!
難道不可以訓練紀律以換取教學成效嗎?
Jones老師在他班上所建立的秩序,不要說是外人,連他自己和他的學生,都為之心動不已。他說:「…我創造出一個充滿權威性的學習環境,而成效卻 看來非常顯著…」;他的學生也說:「瓊斯先生,這是我第一次學到這麼多東西。」,「瓊斯先生,你為何不就都用這種方式教學呢?」…(本篇所有引文皆取自 Ron Jones 所著〈第三浪潮)
但在「浪潮」故事裡,這些師生共有的「明顯進步」,卻被當成納粹或法西斯的表徵;這實在令人困惑,難道拒絕法西斯主義,就得忍受教室秩序的混亂?難道只要教室有了秩序,學生就等於被納粹洗腦了?讓人尤感「尷尬」的是,本來只是想測試學生可以忍受多少軍事訓練,卻意外地帶來「熱心向學」的效果;這豈不是為「教官進駐校園」取得了最合理的藉口?
所以這是一個滿值得追究的問題,讓我們先來近距離地回顧Jones關於此事的描述。一開始,他只是訓練「立正坐姿」、整齊劃一的解散與集合等等,真的就像軍訓課。但為了突顯「領袖」的身份,他要求學生回答的時候,必須口稱「Jones先生」,不可懶散,而且要有禮貌;到此為止,仍然是軍教電影中的常見鏡頭。但緊接著,重點就來了:「回應時的動作變得比內容更重要。為了讓他們牢牢記住這點,我要求他們給的答案不能超過三個字」;而這之所以是「重點」, 是因為這時的「回應」已經不限於紀律訓練,而是悄悄地,不著痕跡地,擴及到「正課」的教學內容去了。
當Jones老師問自己:「我以前怎麼從沒想過要用這種方法?」,他就問到了重點:若不是為了配合紀律訓練,在任何正常的課堂上的討論中,怎麼可能要求學生只回應三個字?僅僅是三個字,能回應什麼?他當然「沒想過」可以這樣,因為「以前」他提給學生的總是須要論述的問題,但現在整個教室的氣氛都變 了:學生都「立正坐」著,全身緊繃,雙眼直視,一個個挺得像個二百五似的,而老師也把自己弄成一個「瞪眼青蛙」式的「教育班長」或「士官長 (sergeant)」;此情此景,老師提的問題,也只能是益智問答式的了。
「益智問答」四字,最能貼切地形容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情境:在電視益智問答節目中,有獎金,有美女或俊男,有觀眾及掌聲,有優勝劣敗的殺伐,有一夕成 名的美夢,搭配著絕對簡單的是非對錯的標準;所有人們能想到的、能提供給年輕人的「有效教育」的條件都具備了,唯獨沒有「智慧」!在搶答的過程裡,參與者 只能在記憶庫裡極為化約的資料中搜尋,雖然展現了極大的搜尋熱情,但任何有關判斷、思考、想像、探索等等要素,也就是和智慧有關的那些,則一項也無!詭異 的是,人們竟稱這種無聊的勾當為「益智」—只怕正好突顯了他們的「反智」的本質。
洞察了這事的反智本質之後,我們就可以明白,根本不需要一位老師;如果是在電視上,一位胡瓜也就足夠了。Jones老師說:「更不可思議的是,就連答案的品質都越來越好,學生似乎也越來越專注聽別人的回應。以前上課不說話的學生也開始參與,越來越多人回答問題」;但他沒有同時提示我們,這兒所謂的答案、回應、參與、回答等等,都已經是這種「反智」遊戲中必然的戲碼(也就是「三字解答」),早就不再是當初追求思想深度的歷史課,是在那種課堂上才能引發 「市民、鐵路列車員、老師和醫生,怎麼可以宣稱他們不知道任何關於集中營和大屠殺的事?」這樣的問題,以致於老師也不知如何回答而必須轉求於「實驗」。
果真是如此嗎?我們有沒有過度解釋而貶損了這場教學奇蹟呢?再看看Jones自己怎麼說的:「學生似乎下定決心要完成我所要求的事項,且精確的複誦 出上課所教的內容與概念」;其中「我所要求」和「複誦」正是精髓,至於「他們甚至問出更好的問題,同學之間看來也更加關愛彼此」,則是在「群體就是力 量」、「行動就是力量」感召之下,群起效忠領袖的自然副作用罷了。
所以,紀律訓練可以換取教學成效嗎?至少從Jones的故事看來,答案就是「不能」,如果我們了解學生應該學得「智慧」,而不是把他們貶抑到反智遊 戲的層次上去!可怕的是,經過這一番細緻的考究,我們不能不發現Jones的所謂實驗,在許多學校裡根本只是常態:他們所一意追求的紀律(軍事化的)和教 學成效(反智遊戲式的),是一體的兩面;二者搭配得天衣無縫,正聯手為將來的法西斯培養潛在的追隨者!
紀律和智慧真的無法並存嗎?
紀律和反智,似乎是真的很「速配」:佛洛姆(E. Fromm)曾說過,凡是生命,都是混亂的,只有在死亡中才能找到秩序;我們可以接著說,智慧是生命的火花,它在「本質上」注定和秩序(或紀律)相衝突。
然而,如果不要那麼刻意地非要談論什麼「本質」(無論它是什麼意思),而運用我們大家共通的經驗和「感覺」,事情恐怕就恰好相反:確實需要某種紀律 (或秩序),才能得到智慧;事實上,Jones在他關於紀律的宣講中也說得很明白:「星期一」的時候,他就舉出運動員,舞者和畫家,甚至科學家,都必須反 覆練習,投入耐心和毅力,並說「這些所需要的就是紀律,一種自我訓練、控制、與意志力。以肉體上的痛苦來換取精神與身體上更佳狀態」。那麼,紀律和智慧的 關係到底是如何呢?
正是在這兒,我們進入教育的核心議題,那就是,必須仔細探究教和學的實質,並追求抽象語詞(例如「並存」、「衝突」等等)的實質內涵。
先拿科學家來說:一個年輕人要想成為一個科學家,他可能首先要把這領域裡已有的研究成果,整理得很有秩序,不但各種數據資料都要分門別類地歸檔,各 項發現的前因後果也必須理得井井有條;但到此為止,他還只完成了一個「研究助理」的工作,距離發揮科學智慧或成為一個科學家還很遠。如果就在這個時候,他 把這份整理紀錄背得滾瓜爛熟,而讓胡瓜先生,不,讓他的前輩科學家用各種「很有紀律」的問題來考試,那麼,他應該就很可以大獲全勝,擊敗對手,脫穎而出; 然而,真正的科學家,應該是在他的手下敗將之中,因為不屑於背誦資料又拙於用三個字回答問題的人,才比較可能成為科學家。
以上說的是,科學的工作當然有其「紀律」的成份,但即使這一成份是不可或缺的,它也並不是科學工作的核心;科學的核心,是創新與發明,也就是其真正 智慧之所在,誰都知道,那絕不是條理化的工作,紀律在其中所能發揮的功能,恐怕非常有限。當然,一個科學家做為一個科學工作者,和任何工作者一樣,都必須遵守一定的紀律,在一定的時間完成實驗,交出報告,參與討論會等等;但這是一個人的「行動」的紀律,並不是指他在思想上,科學思索中,或心智活動(也就是 所謂智慧)的紀律。一般人喜歡強調紀律的要重性,但很少能真正區分紀律的功能是發揮在哪一個面向上,例如,不是發揮在心智活動上,只是發揮在身體行動上。
類似的情形也適用於其它專業領域:一個舞者除了必須很有紀律地練舞,他的舞蹈表現也必須「有紀律」(遵循音樂的節奏,符合既定的舞序等等),這是無 庸贅言的;然而,他之所以成為一個舞者,而不是咕咕鐘上每小時出來舞一圈的機械人偶,正是在他的舞步中的「非紀律」可以侷限或制約的部份。誰都知道,藝術 家無論在生活上,工作上,都必須有紀律,甚至要比常人更有紀律些,這是使他的藝術得以呈現的重要因素;但誰也知道,我們欣賞的是他的藝術,而絕不是他的紀 律。
澄清了這些之後,我們可以回到教與學的問題上來。一個老師應該「協助」學生建立學習的紀律,「營造」班級的課堂紀律,理由已如前述;就此而言,我們 不得不說Jones先生雖然是一位親切又有深度的老師,但他和他所服膺的某些先賢一樣,似乎忽視了紀律在教學上的重要性。當他深自懷疑「…我自己所相信的 開放式學習環境以及自我學習又可以被改變成什麼樣子。我一直以來都相當認同心理學家羅吉斯(Carl Rogers)的想法,但我的信念會乾枯甚至死亡嗎?」,這就表示,他之前並沒有認真思考過「開放式學習」、「自我學習」等概念和紀律之間的關係。事實 上,我們相信他的「禮拜一」宣講,應該就已經把自己嚇了一跳:他假裝宣講紀律之美,沒想到卻擊中了自己的信念、或誤會。
其實在那個年代,許多提倡開放教育的人,都有類似的誤會,以為紀律有違開放;但實際上,所謂開放,應該也適用於「建立紀律」:前文所說的「協助」和 「營造」正是開放式的對於紀律的教導,相對而言,在紀律「訓練」中,學生則是完全被動的,內容又極度貧乏(集中在口令和動作上)。換言之,紀律並非開放的 敵人;開放式的教學,倒是應該將紀律納入—雖然紀律和智慧無涉,甚至相衝突;但這並不妨礙在追求智慧的過程中,在那些非智慧的領域裡,紀律有它的價值。智 慧中雖然容不下紀律;但一個人身體力行的紀律,卻是追求智慧不可少的要素。
讓我們試著簡單描繪如何開放式地教導紀律:其實,紀律美學的宣講,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接下來,當然不該去訓練集體動作,而是可以(例如)讓學生分 享各自的經驗,討論如何使自己的生活或學習更有紀律一些,如果宣講已經發生效果的話。然後,在課堂教學的各個環節上,都可以重覆這些議題,讓學生把紀律也 當成一個可以追求的目標。這樣做,絕不會如訓練坐姿那樣有立即的可見成效,但也絕沒有淪入法西斯主義的危險。
如果教學者對法西斯主義,或秩序迷戀還要更為敏感一些的話,我們也就建議更換名詞;事實上,除了刻意運用傳統語詞的場合,在教育中我們寧可強調「專 注」。無論是舞者或科學家,為了追求各自的境界,真正需要的是專注,有益的紀律往往也只是內在專注的表象;專注是心智的能力,紀律容易讓人產生混淆,特別 是和類似軍事訓練、肢體動作、或身體行為牽扯不清。
說到這兒,讓我們為Jones老師做一些設想:既然在這場實驗中,他已經成功地證明了「我們距離法西斯主義只有五天的距離」;那麼在接下來的教學生涯中,他的任務,不就是要幫助學生把那個距離拉開嗎?這是本文接下來要談論的內容,但我們可以先建議他,在學生已有五天紀律訓練的基礎上,先來展開關於專 注的教學;學生在對比之下,一定深有所獲,而將是一個極好的開始,用來取代對於「第三浪潮」的遺忘,或逃避。(未完待續)
◎本文出自〈人本教育札記〉275期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