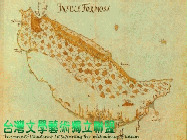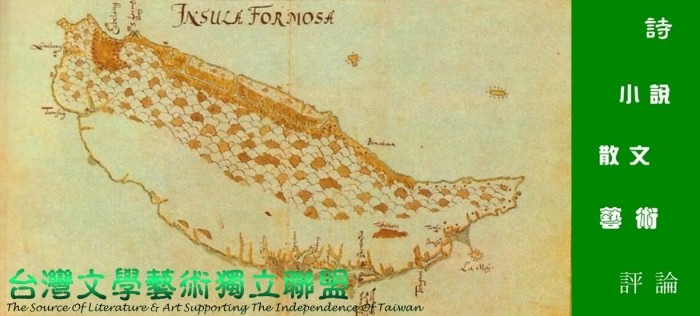多樣語言的文學價值─台灣文學獨立聯盟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ne 22,2011陳秋白─聶魯達「海佮鈴仔〈The Sea And The Bells〉」《一》
聶魯達〈Pablo Neruda〉佇過身的彼年,伊的手頭同時進行八本詩集的編輯工課,按算欲佇1974年7月份過七十歲生日的時陣同時出版。毋閣聶魯達伊並無完成這項工課,伊佇1973年9月份過身,這本詩集內底伊完成號名的詩差不多佔總篇數的三分一。對讀者來講,這是一本誠特殊的詩集,聶魯達透過鈴仔佮海洋意象傳達伊的心靈佮精神,也不時合參愛的情愫。
海佮鈴仔〈The Sea And The Bells〉

1.
起先
一小時閣一小時,毋是日子,〈Hour by hour, the day does not pass,〉
是悲傷閣悲傷:〈it passes sadness by sadness:〉
時間袂起皺紋,〈time does not wrinkle,〉
用袂完:〈it doesn't run out:〉
海,海伊講,〈sea, the sea says,〉
無停睏,〈without rest,〉
土地,土地講:〈earth, the earth says:〉
男子等待。〈man wait.〉
也只有〈And only〉
伊的鈴仔〈his bell〉
佇其它的鈴仔中間〈rings above the others〉
保持空虛〈keeping in its emptiness〉
一種固執的恬靜〈the implacable silence〉
將會綴[tuè]一波一波的湧〈that will be parceled out when〉
湠開伊喊出的金屬的語言。〈its metallic tongue rises, wave after wave.〉
我較早有誠濟物件,〈Once I had so much,〉
跤頭趺行遍天下:〈walking on my knees through the world:〉
佇遮,褪腹體,〈here, naked,〉
除了予人痛苦的海的中晝時〈I have nothing more than the stark noon〉
我一無所有,佮一粒鈴仔。〈of the sea, and one bell.〉
亻因予我亻因承受痛苦的聲音〈They give me their voice to feel the pain〉
佮阻止我的警告。〈and their warning to stop me.〉
這發生佇逐家身上:〈This happens to everybody:〉
空間繼續。〈space goes on.〉
海存活。〈This sea lives〉
鈴仔存在。〈The bells exist.〉
2.
走揣〈To Search〉
對熱狂的歌詩到海的根部〈From the dithyramb to the root of the sea〉
湠出一種新式的空虛:〈stretches a new kind of emptiness:〉
我毋愛濟,湧講,〈I don't want much, the wave says,〉
祇要亻因無繼續講,〈only for them to stop their chatter,〉
城市水泥的鬚芒〈for the city's cement beard〉
無繼續生長:〈to stop growing:〉
阮是孤單的,〈we are alone,〉
最後阮想欲大聲叫,〈we want at last to scream,〉
佇海的面前搖鈴仔,〈to pee facing the ocean,〉
看七隻仝色的海鳥,〈to see seven birds of the same color,〉
三千隻青色的海鷗,〈three thousand green gulls,〉
揣出沙埔頂的愛,〈to seek out love on the sand,〉
共鞋仔,〈to break in our shoes, to dirty〉
冊,帽仔,心智創垃圾〈our books, our hat, our mind〉
一直到阮揣著你,虛無,〈until we find you, nothing〉
一直到阮唚著你,虛無,〈until we kiss you, nothing〉
一直到阮歌頌你,虛無,〈until we sing you, nothing〉
虛無無虛無,無是〈nothing without nothing, without being〉
虛無,無完成〈nothing, without putting an end〉
真實的代誌。〈to truth.〉
3.
轉來〈Returning〉
我有真濟死亡的檔案〈So many profiles of death line my face〉
所以我袂使死,〈that I cannot die,〉
我無法度死,〈I'm not capable of it〉
亻因揣我毋過揣袂著我〈they look for me and can't find me〉
我紮[tsah]走我的物件,〈and I leave with what is mine,〉
佮馬頂我卑微的〈with my poor destiny〉
命運,失落〈on horseback, lost〉
佇無人煙的牧場〈in solitary pastures〉
佇南美洲的南方:〈far south in South America:〉
吹起一陣鋼鐵的風,〈a fiery wind blows in,〉
樹木敧[khi]倒〈the trees are bent down〉
對亻因出生的日子:〈from the day of their birth:〉
亻因要唚土地〈they must kiss the earth〉
柔順的平原:〈that smooth plain:〉
隨後落起〈it come later, the snow〉
千劍雪〈of a thousand swords〉
毋捌停睏。〈that never lets up.〉
我對欲去的所在〈I have returned〉
倒轉來,〈from where I will go〉
佇拜五早〈on Friday tomorrow〉
我共全部的鈴仔〈I came back〉
紮轉來〈with each of my bells〉
也留落來種作〈and I stood waiting〉
走揣牧場,〈searching for the meadow,〉
唚著苦澀的土地〈kissing bitter earth〉
像拗彎的灌木。〈like a bent-over shrub.〉
因為這是義務〈Because it is our duty〉
去服從冬天,〈to obey winter,〉
予風也佇你的體內〈to let the wind grow〉
生長,〈within you as well〉
一直到落雪,〈until the snow falls,〉
今仔日佮逐工合做伙,〈until this day and every day are one,〉
風佮過去,〈the wind and the past,〉
寒冷來到,〈the cold falls,〉
最後阮是孤單的,〈finally we are alone,〉
最後阮將會肅靜。〈and finally we will be silent.〉
感謝。〈Gracias.〉
4.
感謝,小提琴,為今仔日〈I am grateful, violins, for this day〉
演奏的四條弦,純潔〈of four chords. Pure〉
是天的聲音,〈is the sound of the sky,〉
空氣的藍色心聲。〈the blue voice of air.〉
陳寧貴─水涵頭唇介老榕樹
影片連結:www.youtube.com/watch
水涵頭唇介老榕樹
有一頭老榕樹
聽講適阿公以前介阿公時節
百過年前就生在水涵頭唇
大人佇介撂涼唱山歌
細人佇介跋上跋下
佢係者兜小山狗仔介遊樂園
有人用索仔做晃晃
晃來歸熱天介涼風同歡喜
十八歲介年我離鄉後
只有在發夢中
正會佇佢熟識介身項跋上跋下
有時轉老屋家正會去尋佢聊
像睹到老朋友
佢用鬍鬚拍我介肩頭
用樹葉仔摸我介頭那
有一日我盡暢轉去
老榕樹怎會唔見忒
存到硬頸介老樹根
狠狠攬住頭擺古老介地泥
我蓋像聽到當時
斧頭在佢身項鑿出哀嚎
鋸子逼佢濺出
同目汁共樣介屐屎
再過半年後
介老地跡生出
一頭唔會喊唔會笑
我從來唔識介
大樓房
胡長松─台語長篇小說《大港嘴》連載
*本長篇小說獲國家文藝基金會創作補助*
大港嘴 (01)
我感覺真龜怪﹐佇我醒來晉前﹐西爿遠遠的所在親像熠過金iāⁿ-iāⁿ的光﹐有一个柴槌仔底摃釘仔的聲真沈重﹐又閣袂輸有人位嚨喉尚深的所在﹐呼嚕呼嚕嚷出來喝出來的一个假若是阿爸阿爸的叫聲。佇一大群過一大群的查某人的哭聲內面﹐彼束光愈來愈tshîⁿ目﹐尾手佇我醒來晉前﹐它tshioh佇一欉樹仔﹐阿天遂無聲無說必開……
天時hip閣濕﹐燒風kâⁿ佇海的味﹐予規身軀黏thi-thi。
我感覺記智已經欲完全消失去囉。一路我直直想﹐敢講我誠實是位土裡爬出來的——À是位海裡?我毋知。對生命中某一段時間的代誌﹐我總是感覺糊里糊塗﹐想袂起來;閣較好笑的是﹐就算真無簡單想起來﹐嘛一下手就放袂記——總講一句﹐我假若完全是位一場眠夢裡雄雄精神來的﹐除了按呢﹐我的記智實在無通把握啥物。
所以我就行入彎彎khiau-khiau的漉糊糜仔路。路真隘﹐二爿閣ām閣密的野草予人看袂著遠方﹐阿臭樹仔欉佮毋知名的野藤仔花﹐嘛直直佇風中搖顯。
過真久我才遇著人。是一个面仔烏歷歷的歐巴桑﹐伊面的大部分予破糊糊的幼花仔布巾包咧﹐頭戴瓜笠。伊拖一大面漁網行倚來。那面漁網重甲袂輸欲連貼佇土跤﹐又閣親像是位土裡夆硬tshuah--出來的。我知影我已經欲到烏索仔港。
「請問﹐這敢是通到海墘的路?」
「敢講你無生目睭?」
「按呢﹐海墘仔到底閣有外遠?」
「緊矣啦!」
伊頭斡也毋斡就行過我身軀邊﹐阿彼一大面漁網煞閣假若是幔佇伊身軀頂的烏紗仔仝款共伊包稠稠。[i]
……八干拉呀拉呀留﹐請恁坐咧聽呀﹐礁眉加加漢連多羅我洛﹐講起著我的祖先啊﹐親像大魚喔……
晉前猶閣有規山規野的雀鳥仔底飛底啼﹐毋過行過彼个拋荒地﹐就 tshun離離落落幾个寂靜的魚塭仔出現佇我面前﹐tsham幾間仔半浮沉佇土糜--裡的老瓦厝佮幾欉仔孤單、樹葉落盡磅的麻黃爾爾;彼是一幅更加拋荒的景緻。
(阿爸啊!怹到底做啥是誰知咧?規去可憐可憐怹啦﹐就算是我求你好啦……)
(你是誰啊?敢講你無應該較恬咧?)
我假若閣會記媽媽八按呢講過:
「我早就無向望恁老爸矣﹐毋過你起碼要去認你的親小妹﹐若我無記毋著﹐伊今年應當已經十七矣;阿我tshūa你走的時﹐伊才乾焦是三個月大臭奶呆的嬰仔爾爾——你減採閣會記tsit啥﹐著否?」
「我啥物攏袂記矣﹐媽媽!」
「你這个囡仔確實有影乎——敢講你攏想袂起來矣?」
日頭雖然tshu位一爿﹐毋過刺閣毒的光線猶是予我規身軀汗。空氣裡有燠魚的臭臊味﹐親像已經au真久﹐au甲海風按怎吹嘛吹袂散仝款。
「…海流一退﹐所有沙蟳位沙埔仔的土漿裡鑽出來﹐四界攏是那菝仔花甜甜的芳味﹐阿夕陽所照﹐囡仔人快活蹉跎的人影拖甲長長長﹐怹踏海流的跤跡跳舞﹐直到笑聲共每一枝頭毛潑澹……」
He是大熱人的黃昏下晡﹐白鴒鷥孤孤單單佇魚塭仔頂盤踅﹐盡尾牠飛落來﹐歇佇一枝歪tshu̍ah的電報柱。
我是佇一塊青荒的墓仔埔邊遇著彼个魚販的﹐伊身軀kō著的魚鱗佇黃昏的光線下面金熠熠。[ii]
「到彼个青giàng-giàng的沙埔仔﹐港口就無遠咯。」
「您講順這埠岸一直過去﹐就是港口矣是毋?先生。」
「正是矣﹐少年家。你嘛欲位遐去喔?」
「嗯!」
「阿是欲揣人是毋?」
「會使按呢講tsit。」
「若按呢﹐你到底欲揣誰啊?」
「這……我聽講我是佇遮出世的﹐所以乾焦想欲轉來看看咧﹐順續走揣阮老爸佮阮小妹的下落。」
「唉!」
媽媽予我一張相片﹐內面是一个面容憂悶的少婦抱一个嬰仔﹐閣有另外一个細漢查甫囡仔徛佇伊跤邊。當然相片裡的少婦就是我的媽媽﹐阿我呢﹐是一个著青驚的模樣。阮佇沙埔仔頂﹐尻川後是闊莽莽看無邊的大海﹐伊的phú色布裙佇風中飄﹐佮伊鬱卒的面容是真無四配的畫面。
「真難得您猶會記這塊沙埔仔﹐聽您按呢講﹐您應當是久無轉--來矣著否?阿kàu底你走的時是幾歲矣?」
「我無清楚﹐大概四五歲爾。」
「喔!按呢你記智真好呢!其實﹐彼塊沙埔地老早就消失矣﹐阿遐這馬是鎮甲規埠岸的kong-ku-li土角、灌漿的輪皮佮規捆的廢電纜線﹐無按呢袂使﹐若無﹐規个庄仔頭攏會予海湧拆吃落腹--去。」
「哦!敢有hiah嚴重?」
「He當然nooh!這幾年落來﹐海王爺的性地實在變甲太古怪咧﹐一場小雨就予海水做一下灌入庄仔內﹐無帶念半點情﹐一直到這馬猶閣有足濟厝澹漉漉咧。成實是﹐日頭赤焰焰﹐毋過按怎曝嘛曝袂焦﹐規个庄仔頭閣濕閣燙﹐假若一khaⁿ燒氣電鍋咧﹐連死人都棧袂稠!」
「這又閣是按怎講?」
「怹底哼講土裡傷燒hip矣﹐害怹規身軀厚濕疹歹睏﹐一日到晚吐氣pûn - haiⁿ。規庄仔頭攏是這个聲。」[iii]
(喂!講遐濟擺敢講恁攏無聽著?共頭擔起來﹐恁的病就會親像海上的船隻仝款消失去啦。若無﹐嘛至少共恁的目睭thí開啊!)
(我若thí會開﹐敢猶閣叫做破病?成實有影咧!)
麻黃的防風林後面是平波波的海﹐夕陽浮佇海平線﹐嘛假若像是suê佇樹ue中央。我行倚的時﹐一群雀鳥仔位規个攏是落葉的土跤兜著青驚飛起來。
「…咱徛佇埠岸頂﹐看夕陽的光掖落海面﹐阿大海就假若是一座金熠熠的皇宮仝款…」
「毋過﹐媽媽﹐是按怎妳毋家己轉來一紲咧?」
「袂使tsit!因為晉前我講過﹐死嘛無欲轉去彼个鬼所在的。」
「按呢﹐妳又閣是共誰講的啊?」
「我是共我家己講的﹐囡仔﹐你要會記﹐足濟話你共你家己一个人講就有夠矣。」
彼个聲音暗sàm﹐閣遠閣糊﹐假若是那哭那講的﹐媽媽的聲……
「敢欲共我講﹐這个港口是按怎欲號做烏索仔啊?」
「你袂想欲知的啦。」
空闊青荒的港口頭前是幾簇歪tshuah的厝﹐後面是幾間仔古老石硿的厝間﹐tshun厝頂蓋浮佇湳土糜頂懸﹐予真蓊的臭草掩崁起來。夕陽位海的方向照過來﹐遂共怹的影拖甲長長。
老阿婆徛佇埠岸盡尾。伊假若底哭﹐毋過閣聽袂著伊的哭聲﹐乾焦有伊的目屎交落佇土跤叮叮咚咚的聲說。
透風下﹐赤銅仔色的海水卻是恬tsih-tsih閣白蒼蒼﹐看無湧鬚。埠岸內的港面雖然停幾隻漁船﹐不過傾甲真厲害﹐假若夆放捨真久的款。阿若倚近岸邊的水面﹐是船仔的破枝骨佮浮水的柴箍﹐綴海流慢慢仔e-sak過來﹐嘎嘎叫。澹漉漉的埠岸四界崩﹐縫裡塞鹽粒仔﹐佇夕陽的光裡金熠熠。
伊穿規身烏的衫﹐看我行到伊的頭前﹐才款款仔夯頭。
「阮後生是袂轉來矣啦。」伊雄雄共我講。
「哦?」
「你毋知﹐少年家仔。我破病的時﹐伊挑工走到深山林內﹐挽一款lā-hio̍h歇過的樹葉來予我kûn湯飲。」
「成實的?按呢伊人呢?」
「夆掠去矣。予歹人掠去矣。」
「啥物歹人?」
「警察。伊是佇暗暝予一群可惡的警察掠走的。」
「您敢會使共我講?是按怎警察欲掠伊咧?」
「這講來話頭長。伊的船佇盈暗入港﹐續落﹐伊就予人tshūa去矣﹐到taⁿ猶未轉來。怹講伊走私物件。」
「成實有走私的代誌?」
「這哪會有影?我家己的後生我敢毋知?」
伊閣開始哭。
本底我是欲問伊敢有聽過阮老爸的名﹐阿taⁿ這聲﹐我遂毋知欲按怎開嘴較好。我徛佇hia恬恬看伊哭。
過一下仔我才提出勇氣講:
「真失禮﹐我只是來共您探聽一个人的﹐拄才有一位先生共我講﹐入去村--裡﹐凊采問一个攏知的﹐m過想袂到﹐我到旦無看著半个人影。」
我本底想欲講﹐我知影我來毋著所在矣﹐我來﹐本底只是欲完成阮老母的向望的﹐m過﹐佇我面前﹐遂啥物攏無。
「好啦﹐你講﹐你想欲問啥物人?」
「我想欲問一个叫做李碌的人。」
「李碌?」
伊目睭thí大大蕾看我。
「按怎?歐巴桑﹐妳bat伊是m?」
「佇遮﹐無人m-bat伊的。」[iv]
……雨一勁頭落九九八十一工﹐位第一工起﹐逐个人攏認定它無外久就會停的﹐因為已經頭尾有三年沒落雨矣。誰知﹐雨就按呢直直落八十一工﹐落甲人逐逐仔感覺絕望為止。你敢猶會記彼條歌……想當初時黃昏小雨﹐咱倆人相約港邊﹐我看你純情目光﹐目屎直直滴……
「你走啦﹐酒鬼!」
「我欲走去佗?雨已經落四十九工矣﹐你知否?它永遠嘛袂停矣﹐就親像我對你的真情真意。」
「共我的手放開啦!垃圾鬼!」
「等一下你就袂講我垃圾矣!」
「你欲tshūa我去佗位?」
「我欲tshūa妳去QK﹐姑娘。人無睏總是不行的﹐閣再講﹐你hia呢嫷……」
「我欲喝聲矣!」
「妳做妳喝啊!我唱歌予你聽。」
「唉唷!」
岸邊的林投樹林內面是海沙仔舖的床﹐是野草佮螺仔殼舖的床﹐嘛親像是墨汁hiah烏的雨水舖的床。當隔轉天的風雨閣一擺打佇林投樹的葉仔﹐伊澹漉漉的身軀就夆發見un佇hia假若是一蕾拄lian的燈仔花。
「頭家﹐毋好矣。」
「按怎呢?」
「俊少爺伊……伊佇林投樹林hia夆宰死矣……」
「哦?」
彼時陣伊猶穿睏衫﹐乾焦位嚨喉底輕輕仔哼一聲。
「頭家!」
「是閣按怎矣啦?」
「我想﹐是塭仔彼頭的人﹐近來怹是愈來愈囂pai矣!」
伊揚手。
「落去!等一下……你去聯絡司公九仔來。」
「喔﹐好!」
聽講彼工杜鵑鳥直直佇樹頂啼叫﹐假若底念歌﹐歌聲悲切閣哀怨﹐親像是死去親人的哀歌。雨是位媽祖生的時就開始落矣﹐好定閣較早一sut仔﹐位大道公生的時就開始落矣﹐橫直he無要緊﹐你只要知影彼場雨落真久按呢就會使矣。雨是土地的肥底﹐阿當海流漲起來的時﹐也就是天頂眾神考驗--咱的時陣。夯頭三尺總有神明﹐眾生的千苦萬難就親像hiah落佇海裡的雨滴仝款﹐是天予咱的恩。乾焦誠心的人才夠資格有向望。[v]
「毋過﹐司公九﹐是按怎你的查某人欲綴彼个修理馬桶的跤數走矣?對啦﹐我想起來矣﹐嘛是佇彼遍落雨的時敢毋是?」
「這只是因果的報應。伊頂世人是一隻烏狗﹐阿我是伊的主人﹐一工到暗共伊關佇狗籠仔裡﹐毋准伊佮外口的野狗kô-kô纏﹐所以這世人伊轉世做我的某來討伊的公道。」
「原來就是按呢喔。」
聽講司公九仔的老爸司公全仔放的赦馬尚獒走﹐會使跳過三條大溪﹐見若伊搬放赦馬的司公仔戲的時﹐規庄頭的人攏笑咳咳坐咧看。阿司公九仔的老母﹐是天下間尚有司公緣的查某﹐伊嫁予司公全仔﹐閣共伊生九个司公後生。司公九是其中上細漢的一个﹐毋過伊尚有才調﹐嘛是唯一繼承怹老爸通天寶簪的一个。可惜伊拄著一場車禍﹐一枝手骨遂斷去。
「聽講你的司公帽仔頂懸只要插彼个物仔﹐就啥物攏有看。」
「失禮﹐這我無方便講。」
「阿照您看﹐彼个欠我錢無欲還的大頭清仔到底轉--來à袂啦?」
「你是底講啥呀!」
(你這个囡仔﹐我已經講過幾百遍矣﹐是按怎閣欲相信這款連篇的鬼話呢?敢講你猶毋相信我話語--裡的一切?你是按怎毋相信我?敢講我無共彼卷冊翻開袂使?等一下﹐我看一下﹐是馬太抑是路加……對啦﹐應該是最後一卷的啟示敢毋是?)
(是啊!哪會毋是?阿hin是寫啥物呀?)
(唉呀﹐he你雄雄會袂堪得﹐你這个囡仔!怎樣你總是按呢問東問西呢?)
(毋過……)
(你莫閣講矣﹐你只要知影﹐想欲辯解乾焦會予你閣較親像giàn頭爾。相信我!)
漁船仔若是佇早起出海﹐黃昏時就會入港﹐阿若是暗頭仔出海﹐按呢﹐就是佇隔轉工天拍氆光的時入港;閣有﹐有時犯勢伊一出去就永遠袂閣轉來矣——這就是為啥物海邊仔需要hia濟墓牌的緣故。是講這嘛無啥大要緊﹐墓碑下﹐差不多乾焦埋寡衫爾﹐只要一角仔地就有夠矣﹐嘛袂有人來偷偷仔挖墓壙。
「歐巴桑﹐我來﹐乾焦是欲共您問一个人的。」
「唉呀!你náiⁿ毋早講?」
「我拄才早就講矣﹐我來﹐是要找一个叫做李碌的人﹐我的老母共我講﹐這个人是我的老爸。」
「喔!我想起來矣……真害呢﹐náiⁿ按呢講咧講咧就袂記--去?好啦!我共你講﹐毋過佇我講晉前﹐我定著要先講阮後生的代誌。這我猶袂講著否?」
「妳是指伊夆掠走彼tsân是毋?」
「你哪會知?這又閣是siáng共你講的?」
「這敢毋是妳講的?」
囡仔﹐你定著聽過﹐日頭一落海﹐規个烏索仔港就成做一个烏色的港口;有二tsūa烏色親像是老寡婦手骨的埠岸﹐共烏色的海湧箍咧﹐閣有烏色的燈塔﹐烏色的輪機引擎聲﹐烏色的海風﹐烏烏烏﹐位海的方向回流轉來的烏色的酒矸佮烏色的船枋﹐透濫著烏色的歌聲……[vi]
伊倒佇烏mà-mà的床枋頂﹐聽見後生tshi-tshi-tshuh-tshuh穿衫的聲。
「我的子啊﹐你欲去佗?」
「母仔!妳睏啦﹐我佮怹出海一tsūa﹐天光晉前就轉--來矣。」
「你敢無聽著外口彈雷?」
「母仔﹐你免煩惱﹐我真緊就會轉--來矣。」
伊聽著門夆砰一聲關咧。
「……你聽好勢﹐若是你hia kiáu數毋還來﹐按呢阮會予你這世人永遠會記咧﹐你的老母嘛會永遠記咧……」
伊穿雨mua佇落西北雨的巷仔內行﹐直直想這句話﹐閣用手共目尾的目屎púe走。
「好啊﹐無要緊﹐你記咧﹐今仔日我落魄﹐你就按呢待我m﹐嘛袂記咱八是仝生仝死的好兄弟矣m。無要緊﹐有一工我嘛會翻身的﹐時到我定著予你鮮尺仔鮮尺﹐我予你碎骨磨針﹐閣有你彼个水牛連角吞、吃蛇配虎血的烏心頭家﹐好﹐你共我等咧看。」
雨水位壁角直直siap入來﹐順床跤一直爬上伊的床。佇嘩嘩水聲裡﹐伊直直se̍h-se̍h唸:救苦救難南無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普渡眾生地藏王菩薩﹐天上聖母﹐五府王爺﹐太子爺公﹐十八王公﹐二十五淑女﹐西方極樂七十二羅漢……
……秋天一到﹐咱坐佇礁石頂﹐看湧鬚共青翠通光的海菜打佇咱的跤踝。喔妳敢bat聽過﹐咱的祖先是位海的彼爿來﹐是一个美麗珊瑚礁石的島嶼……喂!妳敢有聽著我底講的話?[vii]
「頭家﹐揣無司公九﹐我歸个村揣透透﹐毋過就是揣伊無。這落雨落滴﹐也毋知伊是走去佗死矣。」
「你成實歸个村攏揣透透矣呢?」
「是呀!我m-nà去過怹兜﹐連伊彼間破糊糊的三清宮也去過矣﹐就是看無伊的人。」
「阿芙蓉春咧?你敢去啊?」
「唉呀!我袂記矣。」
「你有影乎!是吃啥物飯的?哪會家己的地盤也毋去巡巡咧?」
「我知矣啦﹐我這馬去。」
賊目阿福行出門的時﹐村內有幾个愛管閒事的查某人傘夯咧﹐坐佇岸邊的石碇頂對伊ti-ti-tuh-tuh。怹看伊行出來﹐挑故意笑甲大細聲。
「狗母﹐看我以後按怎修理恁。」
司公九欠缺一枝手骨﹐毋過遂會凍用伊tshun的另外一枝勇壯的手骨共家己thèⁿ佇芙蓉春的頭牌芙蓉瑪莉身上﹐瑪莉無收伊的錢﹐這誰也管袂著﹐而且伊會佇浴間共伊擦跤脊骿。伊八佇眾人面前講家己完全不是因為司公九斷一枝手臂才同情伊。
「司公九﹐這暫你是攏走去佗啊?我是想你甲強欲死呢!」
「敢真的?瑪莉。」
「當然嘛是真的﹐您也毋較定來。若你定來的話﹐按呢我就得救矣。」
「這按怎講?」
「唉呀!敢講你到旦猶毋知影人對你的心意?我是按呢一日到暗對你日也想暝也望呢。閣有……唉呀!這講著成實予人真歹勢……你底辦彼件代誌的時﹐好親像天頂眾神攏都附佇你身軀仝款﹐全身攏是神力﹐您若是捷來的話﹐按呢我就得救矣。」
「原來是按呢喔﹐瑪莉﹐假使阮某嘛佮妳仝款﹐伊就袂佮彼个修馬桶的走矣。」
「喂!敢講您猶會記恁兜彼个毋八貨的黃酸查某呢?講實在話﹐彼个修馬桶的少年囝仔我是見識過﹐少年罔少年﹐佮你的氣力是無塊比喔﹐敢講有人會欣賞伊彼副軟siô-siô的牲禮?」
「好矣啦﹐三八瑪莉﹐妳雜死矣!」
賊目阿福衝入門的時﹐瑪莉身軀光光當底替司公九穿褲。
「唉呦!你這夭壽骨﹐恁老母無教你是m?」瑪莉那喝那提衫共身軀掩咧。
「臭狗母﹐我才無閒工通睬你。」
伊看司公九:
「祖公仔﹐我總算找著你矣。」
「有啥貴幹?」
「阮頭家請你過去--一tsūa。伊急死矣。」
「我無閒!」
「你無閒?我毋才無閒佮你咧練痟話咧。我共你講﹐你的生理來矣。」
「哦?」
「是按呢﹐阮俊少爺夆宰死矣﹐阮兜頭家要你過--一tsūa。」
「天公有目睭。」
「你講啥?」
「無啥啦。我是講﹐我等一下佮你過。」
厝內面有幾个查某人底哭的聲。怹全圍佇拄洗甲金生的屍體邊仔﹐那哭那為伊念往生咒。李碌穿一su烏西裝﹐拖一雙木屐位房間行出來﹐伊嚷hia查某人﹐要怹小恬一下。
「是按呢啦﹐司公九﹐我要你來﹐就是欲佮你參詳我這个不孝子的法事﹐來替伊超渡一下。」
「伊早就要超渡矣!」
「你講這句話是啥意思?」
「我是講﹐應該的啦﹐人死本底就應該超渡﹐通予伊佇黃泉路較好行--小可﹐閣再講﹐伊hia少年﹐恐驚要佇第十八層的阿鼻地獄滯--一暫。」
「若按呢﹐你就想辦法予伊佇hia較好過--小可啦。我知影你是唯一得著恁老爸真傳的一个﹐代誌辦好勢﹐我會好好仔答謝你。」
「He是當然。毋過敢講你袂記矣﹐阮老爸司公全就是予恁害死的?」[viii]
芙蓉春的頭牌芙蓉瑪莉﹐本名潘雪﹐三十二年華。伊的母親的姊姊﹐也就是伊的大姨﹐彼當年嫁予伊的叔公也就是走私犯潘宗保的細漢舅做細姨。彼時庄仔内的小兒麻痺當底時行﹐阿國民政府當底催sak「麻衫布鞋運動」。伊的叔公是穿麻衫布鞋共伊的大姨娶入門的。伊大部分的時候喝伊大姨﹐阿若叔公佇場的時候﹐伊喝伊嬸婆﹐不過按呢的機會較少小可。另外一點﹐簡單講﹐伊是叫宗保的老阿娘姨婆。
「姨婆!」
「誰呀?」
「是我﹐阿雪。」
「喔!阿雪﹐你哪會有閒來?入來啦!外口雨大﹐緊入來﹐家己揣椅仔坐。」
「姨婆﹐你的目睭是按怎矣啦?」
「無啥物﹐只是有淡薄仔痛。」
「對啦﹐姨婆﹐我媽媽要我提這鍋虱目魚肚湯來﹐我去thn̄g予妳吃。」
「毋免啦。你留咧家己吃啦﹐我吃袂落。」
「姨婆﹐你加減要吃寡物件﹐而且﹐你袂使閣哭矣﹐閣按呢落落去﹐你的目睭會青暝去。保叔會無代誌轉來啦。」
「我的下半輩子全靠伊了﹐阿雪。」
「我知﹐姨婆。」
「按呢你共我講﹐伊的船頂到底載啥物?」
「乾焦是幾箱香菇爾啦﹐姨婆。」
「按呢是按怎怹共我講是會使提來宰人的火槍咧?」
我面頭前的這个老歐八桑閣滴兩滴目屎落來。夕陽的光予海面飄過來的烏雲tsá咧﹐伊的面陷佇深深深的陰影--裡。我閣一遍聽著伊的目屎滴交落佇伊跤邊的聲。[ix]
……八干拉呀拉呀留﹐請恁坐咧聽呀﹐礁眉加加漢連多羅我洛﹐講起著我的祖先啊﹐親像大魚喔﹐礁眉呵干洛呵連﹐呵吱媽描歪呵連刀﹐見若行就行佇前喔﹐外呢英雄啊。於嗎礁舉呀連呵吱嗎﹐到旦我輩子孫不肖啊﹐無羅夏連﹐如風隨舞喔……
「He是啥物聲啊?」
「你敢講聽袂出來﹐遂毋知彼个痟婆閣底唱啥物祖先仔歌--矣啦。」
「啥?你講是誰的祖先啊?」
「嗤!你成實毋知呢?咱的祖先啊!」
聽講痟婆潘阿採嘛是瑪莉的遠親﹐這是瑪莉的老爸潘象共伊講的。潘象的阿公潘來貴佮潘阿採是叔伯兄妹﹐彼時陣﹐當潘象的老爸潘大海予一群提槍的兵tshūa走的時﹐伊嘛是唱這條歌﹐海岸邊的沙土佇歌聲之中絞做一圈螺仔風。
「毋過歌詞裡是按怎講咱不肖呢?」
「敢毋是?你看咱﹐這馬連一塊土地嘛無矣。」
「阿hiah土地是走佗去啊?」
「噓﹐較恬咧!敢講你無生目睭?」
「……你看﹐囡仔﹐阮這款老骨頭的目屎是尚毋值錢的。我只是後悔彼日盈暗無共伊留咧爾﹐假使我共伊留咧的話﹐伊就袂惹遮的代誌矣。我知影he一定是無伊的治代﹐阿講到盡尾﹐這一切攏是彼場無暝無日的雨所致蔭的。」
烏鷌鷌的暝開始罩佇這个港仔村﹐伊講煞徛起身﹐一步仔一步位港邊的方向行轉去。
彼排烏暗的防風樹林雄雄搖顯加亂慘慘。
(有一枝鼓吹佇足遠的所在底pûn﹐假若隔一蕾大大蕾的烏雲。)[x]
聽講一到暗暝﹐港邊李碌名下的小酒館芙蓉春就歌舞太平﹐豬哥酒是hong透暝袂煞。芙蓉春內有十外个嫷姑娘仔獒唱獒跳舞﹐無一个袂解人憂愁。
「毋拘您講毋著一項﹐先生﹐hia毋是逐工攏遮鬧熱的﹐除非是出帆幾個月的船隻入港的時﹐才會有彼款放浪的場面﹐若無﹐平時仔﹐hia姑娘仔嘛是閒加會siān呢!尤其是庄內發生謀殺的代誌了後﹐怹逐个看著軟kô-kô攏親像欲死欲lak-hāiⁿ的形。」
……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暫無休息……
大斂彼日﹐怹共伊的身軀囥入芳貢貢的松梧棺木﹐閣共捲做餅形的金紙掖滇。酒鬼俊仔的媳婦阿慈穿一su純白的孝服﹐哭加欲死欲活。伊的哭聲流湠佇港邊si-si-刷刷的雨聲裡﹐連野狗的目睭攏紅矣﹐假若樹尾的相思仔籽仝款。酒鬼俊仔的媳婦茹頭鬖髻[sàm-kè]﹐跪咧爬到伊的尪婿身邊﹐共伊的嘴倚近死者的耳孔﹐iⁿ-iⁿ-ooⁿh-ooⁿh底講啥﹐真少人聽會清。
……李東俊﹐你這个無心無肝的豬哥標﹐我早就知影你會有今仔日﹐你聽好勢﹐就算你死﹐我一世人嘛袂放你煞……
墓仔埔佇港的北面﹐紅毛土硿龜利糊的埠岸彼箍圍﹐也就是佇通位城鎮的小路的東爿。海流漲過埠岸淹入來﹐阿地下水嘛位幾座墓仔堆之間滇起來。雨水、海流佮地下水洗佇死人疏閣袂爛的頭毛、空空空無仁的目睭﹐閣有海蟲佇怹冷吱吱的骨頭爬出爬入。聽講hia蟲是專治痛風佮烏跤病的﹐怹夆號一个名﹐叫做海枸杞。病人痛落到塊﹐攏到墓仔埔四界揣蟲吃﹐假若野狗仝款。烏鴉徛佇八有四个老查某吊豆過的彼欉林投樹枝﹐嘎嘎嘎底啼唱。怹透暝毋睏﹐唱出欲傳種的歌聲。較早這款病人真濟﹐怹佇眠床頂翻來反去﹐最後只好來遮揣蟲吃。毋拘這款蟲毋是逐日有﹐乾焦佇怹號做風甲雨的大雨的日子才會出現。怹感謝上天﹐佇怹痛苦的時永遠會記予怹希望。
一般來講﹐佇較早﹐大道公﹐也就是老祖的生日彼日﹐海面就會開始khau風。彼日的風會使治百病。風佇埠岸的涵孔內呼呼叫﹐親像是大道公佇佇天頂pûn的品仔聲。祂面目慈悲﹐看袂出來較早乾焦是一个宰豬的。可惜祂無法度共魚販老王的五枝踵頭仔接好勢。話講倒轉來﹐魚販老王是誰嘛袂怪tsit﹐伊的五枝踵頭仔是予家己的大魚刀剁去的﹐閣再講伊是予人位船頂趕上岸的大懶屍兼kiáu鬼﹐全世界乾焦有伊彼个佇巷仔口賣魚羹的伊的某佮芙蓉春的頭家李碌會同情伊。
「老王﹐你敢會佗一工輸加共我賣去?」
「哪有可能?我都毋是魚塭彼爿彼个長工憨順仔kó﹐家己甘願做烏龜、戴綠帽、賣某做大舅。閣再講﹐人總袂永遠輸的﹐算命的共我講﹐今年的偏財運星佮我的本命宮相拄著﹐伊講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呢!」
「尚好是按呢啦。」
魚販老王的破低厝仔是佇港邊魚市場斡入去的巷仔內﹐也就是怹某佇巷仔口賣魚羹的彼一條汰膏爛澇的巷仔。伊出世佇耕者有其田的時代﹐阿真不幸的是﹐伊的家族當初時佇魚塭彼爿有幾分田洋﹐阿怹只好夆逼用hia田洋去換幾張股票廢紙。彼幾張廢紙佇怹兜的衫櫥--裡囥過一个秋天佮規半个冬天﹐一直到某一日有一个城裡的人來﹐開五百箍共買去﹐怹才又閣共錢投資佇充滿向望的烏魚頂懸。毋過he是一个拍交落的向望。彼年寒流來加傷晚﹐掠無魚﹐伊的老爸最後乾焦掠著兩尾烏魚。為著這層﹐彼个可憐的人到死晉前一直活佇米酒裡。講落到塊﹐魚販老王身上有上百个缺點﹐毋過伊有一个優點﹐就是共這个教示記牢牢毋lim酒。伊閣有一个優點﹐就是有時仔看起來好親像是一个真正的查甫子。
「老王﹐你共二指剁去﹐敢袂痛?」
「袂痛nooh﹐完全袂痛nooh。你聽好勢﹐後擺我若閣去púa﹐就共中指嘛剁掉。」
「毋過你乾焦tshun四枝踵頭仔--爾呢。」[xi]
親像一到暗暝﹐烏索仔港的血色就逐逐仔恢復﹐老先生揪的弦仔全是鄉愁。
「老先生﹐你的弦仔揪加太好咧﹐毋過﹐是按怎你毋唱一條歌來聽看覓咧?」
「你獒問﹐囡仔!是按怎我毋唱一條歌咧?」
雨綿綿精精落八十一工﹐無nooh﹐好定要講真壓霸無理﹐按呢落八十一工﹐定著是閣較久--小可。雨一落﹐酒鬼俊仔佮伊的王兄柳弟就 tshūa hia天真無邪的少女﹐跳入落碇的漁船仔裡汰膏代盡舞。土水工阿木的查某子春豔就是其中一个。伊袂曉讀書﹐毋過美麗大方﹐性格開朗﹐真會曉體會生活的樂暢。
「春豔﹐妳敢敢坐我的船?」
「加講的!」
「春豔﹐妳敢願意陪阮遮兄弟飲兩杯?」
「當然咯!」
「春豔﹐妳想阮tshūa帶妳來快活一下啥款?」
「好啊!」
半暝﹐土水工仔阿木氣phut-phut走去芙蓉春鬧場。伊空手白拳佇雨裡iⁿh-ooⁿh嚷﹐予一个穿西裝的少年家仔擋佇門外。伊受氣的時一向是青面獠牙﹐花筋齊浮﹐毋過遂無人會驚伊﹐除了伊的某﹐也就是港邊的漁網仔工秋菊。秋菊是好性地的查某﹐伊吃拳頭母準做吃補﹐予尪婿日也推暝也拍﹐一直到伊火氣齊tháu。毋過彼工就算是按呢嘛無法度tháu阿木仔的一腹火﹐所以伊直接lòng到芙蓉春來。
「叫彼个姓李的出來!閣有伊的彼幾个龜仔子。」
「大哥﹐你有何貴幹呢?」
「鬼幹?你就去講﹐恁爸要怹尻川開花﹐按呢知否?」
「喔!原來如此。遵命!你請佇遮小等--一下﹐我入去請怹出來。」
續落徛佇伊面前的﹐若講是一群人﹐閣較輸講是一群提傢俬箠仔的虎狼豹彪。隔日天光﹐伊規身是傷﹐siān嘟嘟欲行去做工﹐二枝跤腿的紗布纏按按。
「唉呦呦!阿木仔!阿你的跤是按怎矣?」工頭土泉仔問伊。
「沒啥﹐昨昏行路的時跋倒的。」
「行路要較細膩咧啊!你按呢是欲按怎做空缺咧?」
「我知影矣!」[xii]